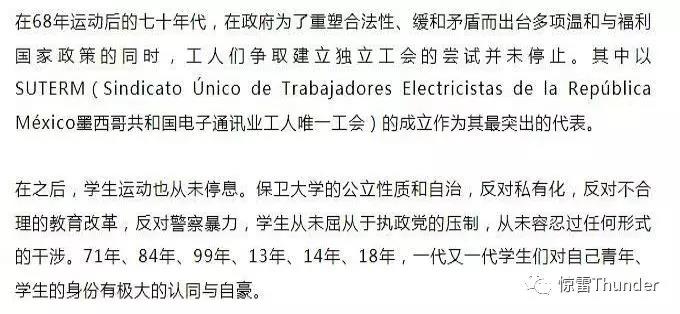不革命的中产知识分子和他们眼中的女人
小武 著

1. 中产阶级|玻璃窗|革命
阿方索·卡隆,这位墨西哥籍的好莱坞导演声称要用影像来描述1968-1971年墨西哥革命对自己生命的刻画和改变。这种尝试目前看来似乎是大获成功,奖项接踵而至,媒体好评不断。但亲历过那段革命的墨西哥革命者,大概要感到失望和不公允。无论如何,导演作为中产阶级大家庭的一份子,始终站在革命的外部来俯瞰和遥望。
影片91:50—96:50,这是直接展现革命的五分钟,充斥着对革命的粗浅想象:标语、人群、枪。没有针对革命者的正面镜头。革命者不仅失语,而且缺乏具体的容貌。一群不知从何而来,也不知去往何处的人群,站在大街上,刚刚向前行进,突然向后逃亡。接下去是杀戮,眼泪。那位抱着死去男人哭泣的女性替导演喊出了心声:“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革命?还是为什么杀戮?导演显然说的是后者。而对前者,他表示不知道。一片茫然,无法理解,不可理喻。他和革命始终隔着一道玻璃窗——汽车玻璃,或是建筑玻璃。
注意94:40-95:00,镜头通过摇移将家具店玻璃窗外的大街“骚动”展现在观众面前。这不是一个足够“安全”的场景,导演心知肚明。如果不用玻璃窗将混乱无序的对峙与他的观众做一个隔离,他们一定会被吓坏的。这就是中产阶级镜头应处的空间位置。就这一点来说,《罗马》配得上它所获得的一打奖项。
中产阶级:汽车内 家具店里 家中
革命群众:汽车外 家具店外 大街

接下来,95:10-96:00,革命表现为一种闯入:破坏。怀孕的女佣克里奥和雇主家的奶奶在家具店选购婴儿床,但被一起对革命者的追杀事件打断,最终克里奥产下死婴。辩护者也许要为导演的意图进行解释,诸如克里奥的前男友费尔明实际上隐喻着美国支持下的墨西哥独裁力量,而克里奥的死婴象征着革命的流产,导演以此来表达同情。不必反驳,但同情,不过是同情而已。实际上,同情是中产阶级的专属自慰器。底层革命者是没有资格同情的。如果一个人有十分的冷酷,就表现出十分来,而不要用别的什么去掩盖一部分。
因此,革命者的缺席又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导演可以告诉你他从这段作为局外人的生命经历里得出的道理:革命——残酷但无用;让我们用别的办法解决问题吧!
(“革命者也不勇敢,同志们,他们只会逃跑;而对面是很强大的——92:55-93:20是一个展现警察力量的平移长镜头,我们投降吧。”)
2. 女性|家庭|外部
阿方索先生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女人,一个看似非常激进的思路。

让我们来到122:48-123:28,大概是全片最“感人”和“催泪”的一幕:从海浪里救下了雇主孩子的克里奥和雇主一家人相拥而泣,得到安慰后,克里奥失去孩子的心结也得以解开。这大概就是——爱,一种既让人无法相信也难以认同的爱。以此幕作为整部电影的海报,也算是切中宏旨。因为矛盾从来都没有得到过解决。女主人索菲亚和佣人克里奥,她们的地位差异不会因为一次海边煽情表演或是家庭聚餐、度假就得以抹平。所谓“共克时艰”,是当上层陷于麻烦而底层利用价值增大时,前者不得不营造出来的说辞。面对丈夫的抛弃,索菲亚难道有别的更为经济的选择吗?而对于克里奥来说,她从怀孕开始就担心被解雇,这种焦虑的根由不言自明。
何况,两种不同的心事根本上也无法互相分担。注意:将雇主丈夫对索菲亚的离弃与费尔明对克里奥的离弃划上等号是不合理的。在导演的引导下,我们似乎倾向于认为,电影是两个同样被不忠诚的男人抛弃的女人的故事,她们的痛苦来源于男性。但索菲亚的丈夫作为一个高薪医生(同时也是白人精英)和费尔明作为一个乡村土著,他们面临的问题是完全不同的。因而,当这一家人和克里奥相拥而泣时,他们只是为自己哭泣,而并不明白社会的另一端发生了什么。就像电影中呈现的那样,索菲亚的世界里压根没有革命。如果我们把爱定义为使利益最大化而进行计算的关系,那么我非常认同电影海报呈现的场景,它展现出导演的阶层底色。
因而,这是一个中产阶级臆造出的女性乌托邦。在去年的国产电影《找到你》中,也可以发现这类乌托邦短暂的闪现。和《找到你》中的保姆不同的是,克里奥作为一个年轻女性没有婚姻和家庭,这使她可以更加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对雇主家庭的服务中去。必须要指出这残忍的一点。
现在我们可以来总结《罗马》如何用男性和女性的性别对立解构了阶级对立。
阶级对立关系
雇主/白人精英/中产:索菲亚和她的丈夫
仆人/原住民/底层:克里奥和男友费尔明
性别对立关系
男性:索菲亚的丈夫和费尔明——背叛 暴力 好斗 怯懦 专断 社会
女性:索菲亚和克里奥———— 忠诚 爱 平和 勇敢 包容 家庭
在导演那里,最终似乎第二种对立关系战胜了第一种,从而更有说服力。但恰恰是这种处理遮蔽了墨西哥社会大量问题的根源。也正是基于这种性别对立,女性被处理成一个蜷缩于家庭,面对社会动荡茫然无助甚至麻木迟钝的被动形象。在这里,海边的相拥似乎也标志着传统家庭的重建——男主人的出走只意味着等待另一个男主人的降临。这种女性形象与其说是女权主义的,不如说是父权主义的变体,是男性强加于女性的想象。我们是否可以期待一种真正的女性革命者形象呢?这种形象在《罗马》中是绝对缺席的,尽管她在历史现实中绝对存在。
3. 革命|爱 或 革命之外没有爱
现在我们终于谈到了革命与爱的关系。在导演阿方索那里,爱是跨越阶级的存在。它最后试图在电影里得到证明。但本文全力以赴地反对这个结论。
克里奥并没有从这个中产阶级家庭那里得到爱。33:40-36:20:丈夫→妻子→佣人×→狗,这是一个因为狗屎而起的迁怒/压迫链条,但克里奥作为鄙视链的最底端,并没有将愤怒抛向狗。孩子们又受到怎样的教育呢?他们经常因为一点小东西而争吵,要最大的,最多的,最快的,最好的。而奶奶的解决办法是,告诉他们玩具和食物还有很多。几乎没有希望看到他们对公平(这是爱的基础)的真正理解。而贴满房间的海报(mexico68,mexico70),叙述的是墨西哥上流社会的荣光:奥运会和世界杯。他们并不理解另一个世界的克里奥。就像导演阿方索也不会真的理解他童年时期的女仆那样。
不过,克里奥同样没有从费尔明那里得到爱。不仅如此,费尔明作为革命的(被利用的)镇压者,尽管是身处革命之人,却是个反革命者。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一对核心关系,实际上展现一个身处革命之外的女佣和一个反革命者的故事。这些人被革命波及而不是革命的正向参与者。但由此可见,即便在同一阶级内部,如果缺乏革命,爱也是稀缺。而这种革命,是针对一切不平等关系而言的,既包括阶级革命,也包括性别革命。
但《罗马》选择不展现革命者的爱情故事。爱被放置在革命之外而被讨论。要知道就在2018年,墨西哥又爆发了新一轮的运动。这种革命之爱,什么时候会被呈现在镜头下呢?
.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