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前日本经济危机及其后果 ——权贵资本主义案例研究
淳风 著
1912 年,明治天皇去世,皇太子嘉仁即位,取易经“大亨以正,天之道也”之意,改元“大正”。彼时的日本,通过两次战争豪赌,已经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作为英国在东亚地区倚重的盟友, 融入以大英帝国为核心的国际融资与贸易体系,赶上了上世纪初帝国极盛期的全球化浪潮,坐享不列颠治世(PAX BRITANNICA)的和平红利。
与政治军事上的夺目成绩相比,日本经济发展只能说差强人意,缓慢的内部资本积累进程使重工业部门尚未脱离萌芽阶段,对外贸易中日本所能供应的纺织品与杂货拓展市场也十分艰难,有限的创汇收入应付日俄战争时期借入的沉重外债也倍感吃力。及至 1914 年,该年日本外债存量近 20 亿日元,而央行掌握的硬通货扣除发行准备后不足 1.5 亿日元,已不足以支付当年到期的外债本息,从而形成了严重的国际收支危机,债务违约似乎已不可避免。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犹如天佑神助,拯救了悬崖边缘的日本经济。
交战国战时需求,以及列强商品退出东亚市场后留下的广阔空间,使日本对外贸易的局面发生了魔术般变化,净出口自 1915 年起转为巨额盈余,其后连年暴增, 1914~1920 年,纺织业的重要产品棉布,出口金额由 3400 万日元激增至 3.3亿日元,商船队规模由战前的 7.8 万吨,增至 1918年的 51.3 万吨,总吨位攀升至世界第三,也为日本带来巨额海运费收入。
与某新兴强国新世纪以来的发展逻辑相同,国际市场空间与大量剩余劳动力的结合促成了外贸爆发,而贸易部门的爆炸式发展带来就业机会并积累大量资金,进而扩大了国内消费与基建投资,进口来源的断绝,带来巨大的重化工业产品进口替代需求,日本机械、化工产业也进入了加速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国内投资年均增速达到惊人的 26.5%。在最高峰的 1917 年,净出口占日本国民生产总值比重为 10.9%,相比之下,中国 2002年入世后所经历的外贸黄金十年里,净出口占GDP 比重最高也“仅”约 8%。
日本的巨额贸易顺差一直延续至1919年,利用经常收支上积累的盈余,通过为英法等交战国提供融资,日本一举由违约在即的重债国,转变为净债权国,日本的官方外汇储备,在 1919 年末也达到了 21.8 亿日元,相当于当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的 10%以上。
日本奇迹是一个典型的权贵资本主义崛起之路,在将国内劳动力兑现为资本的过程中,获益最多的是传统财阀、华族势力,面对资本过剩这一幸福的烦恼,器小易盈的日本官方与财阀大手笔对外输出资本,迅速成为当时民国无担保外债最大的债权国,至北洋倒台,未偿本息仍有 6 亿日元之巨,形成其后旷日持久的中日债务纠纷。
随着世界大战的落幕,战后日本向何处去?作为既有国际秩序最大的受益者之一,彼时之日本对于与英美协调尚有着清醒的认识,其战后外交取向,是在合作的基础上,依靠自身新晋大国地位,寻求有利于己的东亚战后国际体系,正如革新派官僚鼻祖之一后藤新平在大战结束前夕所言:“我国与列强为伍参与世界大政策以此次为开端,弄潮于世界向日本时代转向的大变革浪潮之中,与欧美各国同舟共济之机会亦自今日始”
随着日本一战后一跃跻身国联五大常任理事国,并在华盛顿和会上成功获得列强对其东亚区域强国地位的确认,日本基本实现了其所期望的战略目标。


而在日本社会内部,一方面,比较优势产业的发展是建立在对劳动力的残酷剥削之上,类似夏衍笔下《包身工》中日资企业女工的生活,在日本本土更为变本加厉,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另一方面,日本的发展“奇迹”令一部分知识分子醉心不已,开始寻找有别于传统自由主义的思想资源和理论解释,这种从一开始就步入歧途的自我塑造尝试,内嵌着与外部世界冲突的结构性因素1918 年 10 月,大川周明等人成立民间文化沙龙老壮会,成为日后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最初起点。
经济上,战后出口热的退潮势所难免,英美资本重返亚太后,日本出口增长明显减速,仅以中国市场为例,随着民国与英美一般贸易的快速恢复,战后日本在中国贸易中所占比重由 1919 年的 36.34%下降到 1921 年的 22.55%,而英国则从9.46%恢复到 16.07%,美国从 16.23%增长到18.84%。另一方面,庞大的国内投资使进口资本品与原材料的需求居高不下,上述因素共同作用使日本贸易收支于 1919 年转为赤字,赤字规模其后更连年扩大。
对外贸易的这一变化绝非日本特例,由于劳动力、储蓄等经济变量的动态变化,一个经济体贸易的大量盈余必然难以长期维持,事实上,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经济也走过了近乎相同的轨迹,其一般贸易项下自 2009 年后即转入巨额赤字状态。
为了维持景气, 1918 年上台的政友会内阁推出了大手笔财政刺激计划,地方政府的基建投资也持续高涨。当贸易红利效益下降后,出口导向向内需拉动的转型方向似乎顺理成章,处于城市化初期的日本经济搭配充裕政府财力,投资拉动的空间看起来无限广阔。
这一思维的盲点在于将超常规增长阶段的体验外推,对政策搭配形成路径依赖,认为自身模式已超脱经济周期,对结构调整过度自信,一旦发展遭遇挫折,则从政策当局到社会层面的准备都是不充分的,在棘手的政治经济压力面前,统治阶级将矛盾对外转移将成为必然。
1920 年,美国恢复战时中止的金本位货币制,由此导致的通货紧缩使美国经济陷入短暂萧条,由于日本出口对于美国市场的高度依赖,这一冲击向日本国内快速传导,东京、大阪股市暴跌,一度暂停交易达 30 天,这次危机后,日本社会一战以来延续的亢奋气氛为之一变,贯穿整个二十年代的慢性萧条拉开了帷幕。
从宏观指标上看,日本 20 年代依然成功维持了高速增长,十年间, GDP 增速仅次于美国位列世界第二,重化工业迅猛发展,实际工业增速在世界主要国家中首屈一指,甚至超过苏联同期水平,经济增长的主要发动机是国内投资,这其中与政府关系密切的财阀企业一马当先,这类企业占据着各种最有利可图的资源性、垄断性行业,根据战前统计资料,日本主要公司中约三分之一为财阀企业,在矿业、有色、机械、房地产等高利润行业中占比更是达到七成以上,依靠关联银行的特殊关照(被时人称为 “机关金库”),这类企业获取信贷资源也远比一般企业容易得多。
然而投资所能提供的迂回空间是有限度的,所形成的生产能力最终依然要顺着产业链条依靠下游市场消化,一旦外部需求放缓,则必将形成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这正是 20 年代初日本经济所面临的挑战。除了企业产能过剩,地方政府基建投资的冲动在 20 年代也快速膨胀,地方财政支出占比,由 10 年代末的 30%,增加至 20 年代末的 50%。

面对经济过热见顶,调整自然是一种共识,不过刚刚经历高速增长期的社会,从上到下对于经济下行周期的到来事实上都抱有一种叶公好龙的态度,任何一届政党内阁,都难以承受泡沫破裂的政治代价,只能采取水多加面,面对加水的微调政策维持泡沫不使破裂。
大量僵尸企业依靠关联银行贷款维系生存,投资与信贷日益形成自我循环,也造成日本银行业的存贷比持续紧张,吸储困难之下,不得不日益依赖同业拆借市场融资,借短放长造成明显的期限错配,企业所积累的不良资产也转化成了银行部门的庞大呆坏账。
面对银行业的严峻局面,日本央行成了疲于奔命的“裱糊匠”,关东大地震后,日银推出震灾特别融通窗口,为受灾企业提供定向货币宽松,避免信用链条断裂,然而这一措施很快变成变相的全面放水,这种为刚性兑付背书的行为,进一步助长了投机行为。直至 1927 年,日本央行试图收紧票据贴现条件,却使台湾银行的巨额坏账暴露,一举爆发战前日本最严重的银行危机。
工业与基础设施投资,除利用国内银行信贷外,也开始大量借入外债。 1923~1929 年,外债规模已达到了 13 亿日元。日本所面对的国际资本流动风险也随之加大。
投资率的不断增长必然压缩消费率,而投资泡沫越滚越大的同时,企业盈利能力反而持续恶化,用工需求减少,吸纳新增劳动力的能力下降,慢性萧条的后果在20年代后半期显性化,据1926年统计,当时在日本薪俸为生家庭中,有80%入不敷出,同期,大学与专门学校毕业生也出现严重的就业问题,“毕业即失业”成为普遍现象,至20年代末期就业率已不足40%。中间阶层的生活状况大大恶化,青年人口向上流动的难度增大,与此同时,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必然导致收入分配向资本的过度倾斜,20 年代日本基尼系数直线上升,一度达到0.6 的超高水平,贫富差距日益悬殊。
经济的长期萧条无法不对社会生活产生影响。
1921 年,发生了退伍军人朝日平吾刺杀大财阀安田善次郎,并随后自杀的爆炸性事件,引起社会极大震动,可以说是日后大量类似事件的先声,在朝日所写的遗书《死亡呐喊》中,集中表现了当时底层日本青年对社会现状的不满情绪:“奸商安田虽积巨富,却不尽富豪责任,无视国家社会。因而加以天诛以为世之警示”“有的赤子因劳动过度,生活环境污秽,营养不良而患肺病,有的赤子丈夫死后为养育爱子而卖淫,有的赤子唯有在战时被捧为国之干城,负伤变为残疾人而等同乞丐卖药为生,有的赤子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都在街头奔忙徘徊,有的赤子因食不果腹触犯轻罪而在监狱里烦恼,相反达官贵人虽犯大罪却能操控法律免受处罚。”
进入社会矛盾高发期后,面对内外部环境的重大变化,日本国内各利益集团对改革的必要性有直觉的认识,却对改革的方向和路径缺乏理性与系统的共识,明治时代以来政坛前台的几大势力,军头、政党、重臣,由于其在国际国内事务上的经验积累,决策与行为方式潜移默化地向主流文明世界趋同,在一战后的日本社会,传统实权集团事实上成为了最重要的开明派力量,成为日本政治走向不脱轨的最后保险。

吊诡的是,传统实权集团为避免政治代价而竭力维持经济泡沫,然而慢性萧条对社会的消耗,依然极大削弱了这一集团的民意基础,另一方面,组成明治体制的其他边缘利益集团,尤其是宫廷、华族和军部内反长州阀势力,出于争夺权力的需要,逐渐有意识地开始在法西斯主义中寻找理论依据和政策出路。
1919 年,长期参与同盟会地下活动的日本浪人北一辉目睹五四运动,东亚共荣理想幻灭之下在上海闭关四十余天,炮制出日后日本法西斯夺权与国家改造的总纲领《日本改造法案大纲》,这部逻辑混乱东拼西凑的大杂烩,对于一部分躁动不安而又苦无出路的日本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其实质意义,是为日本权贵资产阶级提供了一整套转移内部矛盾的议题与话语体系。
对于日本与旧列强之间的利益折冲,北一辉以一种强烈的受害妄想写道“彼等就应无条件承认国际无产者之日本,充实以实力组织起来之结社—陆海军,进而诉诸战争匡正非正义之国际划界。假若此为侵略主义,军国主义,那么日本就应在全世界无产者阶级欢呼雀跃声中,加冕此黄金之冕。”
北一辉将国际事务上的野蛮和专横视为大国崛起的标志,将践踏国际体系视为强国的特权,“百年以后,我国人口将达两亿四五千万,需要能够养育这些人口的大面积国土,因此不可能安居于和平论,需要民族竞争,国家竞争,为此我们要把宝剑的福音,即武力看成神圣,这样,在国家改造后,必须执亚洲乃至世界之牛耳。”
就是这样一篇精神病人的呓语,却在日本国内极端思潮的小圈子里被奉为圣典,北一辉也一跃成为愤青圈中教父级的人物。回到国内的北一辉,很快与大川周明联合,将沙龙性质的老壮会改组为极端色彩更加鲜明的犹存社,有意识地向青年军官和大学生群体扩散其思想。
对日本走向军国主义更关键的因素,是上层权贵圈中的边缘派系,对法西斯思潮抱着利用的态度姑息培养。
1921年,在标志着元老政治式微的“宫中某重大事件”中,头山满和内田良平等右翼黑社会大佬即与皇太子裕仁身边的宫廷集团密切合作,共同对抗山县有朋。或许是在这次事件中尝到了豢养极端势力的甜头, 1923 年开始,宫内省在原皇居内旧中央气象台遗址设立了社会教育研究所教育部(大学寮),负责该机构日常事务的,恰恰是大川周明在犹存社告终后成立的行地社。利用这一上流社会的交际平台,内大臣牧野伸显,反长州军人荒木贞夫等奔走其间,为权贵圈子的结盟与站队做了充分铺垫。
在陆军内部,随着山县有朋去世,两股新势力迅速崛起,一派是上原勇作所缔造的新军头派系上原阀(亦有佐贺阀之称),继承人包括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另一派是以巴登巴登集团为代表的陆军青年军官团体,这一集团源于裕仁皇太子访欧期间对青年陆军留学生的接见,也成为宫廷集团掌握军队的后手。在围剿了长州阀之后,这一新兴权力集团如同见血的饿犬,急不可耐地将下一个目标对准现行政党体制。

20 年代长期经济萧条导致的阶层固化与贫富差距日益悬殊,使大量日本青年成为法西斯思潮的追随者,为大国崛起摇舌呐喊,坚信英美鬼畜害怕神州日本崛起,破坏日本主导的东亚区域安全体系建设,拉拢支那形成对日本的 ABCD 环形战略包围圈,国内的种种乱象也是动辄鼓吹英美民主自由的日奸国贼败坏的,这样简单直白的阴谋论洗脑对底层青年表现出十足的吸引力,成为转移青年不满情绪的最佳渠道。
数量日益庞大的粉丝群体也是一座发财的金矿,例如北一辉这位教父级“意见领袖”,凭借其舆论影响力四处靠造谣辟谣勒索财阀与官僚,形成一门日进斗金的舆论水军生意,这个落魄大陆的穷浪人在 20 年代过上了起居八座的富豪生活。雄厚的财力与名气,又得以帮助他们进一步跻身上流社会圈子,寻找更大政治投机的机会,北一辉及其弟子西田税从勒索财阀与官僚得到的充足经费,也使其逐渐向军队青年官兵渗透。 20年代中后期起,北一辉的豪宅就变成了东京驻军青年军官梦寐以求的享乐俱乐部。
忽悠底层群众想卖个好价钱的在野“思想家”,与寻求理论工具和社会基础的上层利益集团相结合,通过拨弄民意将会爆发出巨大的力量。
1929 年,身负重任的滨口雄幸内阁终于做出了金解禁的决策,恢复日本自 1917 年后中止的金本位体制,相当于断然实施紧缩性政策,其背景是日本投资泡沫已经滚动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沉重外债导致再次出现了外汇储备的枯竭,政府和日本银行持有的硬通货由 1910 年末的 21.8 亿日元下降到 1929 年末的 12 亿日元。扣除日本银行券的发行准备, 1929 年末外汇资产只有 1.4 亿日元,接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国际收支危机时(1914 年)1.2亿日元。
滨口雄幸的目标还不止于此,曾经作为加藤高明内阁大藏大臣,主导20年代中期后一系列经济改革的滨口,对于国际协调有着清醒的认识,1928年上台的滨口雄幸内阁,可以说代表了战前日本国内开明力量最后一次试图挽救经济,协调国际关系的努力,在滨口任内,对内紧缩财政开支,裁减军费,撤除对僵尸企业的保护,加速过剩产能调整,对外则试图与英美达成妥协,以换取贸易与融资空间,1930年伦敦条约的签订就是这一努力的顶峰。
然而,长期隐性经济危机造成的分配失衡,使市民阶层这一大正民主的基石不断削弱,而边缘政治势力野心和流行于底层愤青中的法西斯思潮相结合所爆发的盲动力量快速膨胀,已经注定了这次改革闯关的失败,而正好发生在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最终使这种权力转移以最惨烈的方式完成了。
日本按旧平价实施的金解禁,事实上相当于本币大幅升值,这一因素叠加空前绝后的大萧条爆发,日本的国际收支崩溃了。金解禁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使战前日本经济的各种内在矛盾一举表面化,1929~1931年,形成了日本现代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1929~1932年,以货物价值计算的全世界范围内国际贸易总量下降了65%以上。日本最依赖的海外市场美国在经济危机打击下购买力急剧下降,再加上1930年起美国开始着手实施贸易保护措施,把日本进口商品的关税平均提高了23%,使日美贸易形势不断恶化。1930 年美国进口的日本商品总额为27亿美元,1931年降到2亿美元,1932 年又降到1.3亿美元,1933年降到1.2亿美元。日美贸易中对日本经济影响最大的是生丝贸易,到 1934 年,生丝在日本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率已从危机前的42%下降到只有18%生丝危机进一步向国内纺织业和原料供应部门传导。大量纺织业工人失业或无法拿到工资,而为这些工厂提供原料的二百多万户养蚕农户,约占日本全部农户总数的40%。据1929年日本帝国农会的调查,当年全国农家负债总额达45.85亿日元,1932年又增加到54.98亿日元,这些数字相当于日本农产品生产总值的2.7~3.25倍。差不多每户农家平均负债达 900 日元左右。同期发生的东北地区自然灾害使农村情况更加不堪,甚至出现了东北部农民被迫将女儿卖入妓院等极度刺激公众情绪的事件。
从金解禁开始到1931年9月英国放弃金本位制,由于对日本经济的极度悲观预期,资本外逃的现象失控,1930~1931年黄金流出额合计达到了8亿日元以上。1930~1931年,推断日本城市人口失业率已高达15~20%,原有经济与政治体制濒临崩溃,蠢蠢欲动的各路边缘政治势力嗅到权力摇动的气息,如同嗜血的野兽一般猛扑了上来。

1930年,政党内阁顶着国内政治的重重压力,强行签订伦敦条约,成为刺激法西斯势力暴走的催化剂,海军谈判代表财部彪在返回东京时,一下火车便收到了自杀建议书,1930 年底的日本,弥漫着此前未有的恐怖气氛。
1930年11月14日,滨口遇刺重伤,强撑病体与各路势力周旋的滨口最终因伤势复发于次年8 月去世,滨口雄幸的死,也标志着日本开明派最后的改革努力宣告失败,惶恐不安的各大财阀转而开始大力资助极端势力,法西斯全面掌权的前景已告明朗。
1931~1936年,是日本法西斯化的建设与过渡阶段。混乱中得以进入权力核心的各个利益集团需要时间熟悉政治运行,社会舆论和文化要一元化,皇道化,更重要的是,在夺权目标下联合起来的各路势力,为权力的分配必然将产生激烈的冲撞。
作为昭和新格局下最强大的政治势力,陆军内部以荒木贞夫为首的上原阀老军头和军部佐级军官的小集团矛盾日益激化,分化为皇道派和统制派两股势力,对上原阀坐大的警惕使宫廷集团大力扶持统制派势力,由此也成为皇道派的对立面。
在这一过渡阶段,经济泡沫破裂后的日本经济反倒开始了复苏。
1931年8月,滨口雄幸去世,9月,918事件爆发,12月,面对硬通货的急剧流失,已经年过七旬,久负盛名的高桥是清重新上台收拾局面,日本宣布退出金本位体制,采用激烈的货币贬值与资本管制,终于平息了严重的资本外流危机。
在被誉为日本凯恩斯的高桥是清扩张性政策刺激下,结合为战争动员需要大强度的重工业投资,日本经济在1932年后逐渐复苏,在低利率、低汇率及财政扩张的刺激下,30年代初的日本社会好像打了吗啡的重伤员一样,弥漫着一股乐观的气氛,日本似乎已经在主要大国中第一个走出了大萧条的阴影。依靠价格管制,组织卡特尔等行政命令手段,国内物价稳定,就业回升,出口也因货币贬值而得到改善,1933年后,日本正式超过英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棉制品出口国,实际人均 GDP 迅猛增长。
在 30 年代的畸形经济复苏中,收益最大的仍然是财阀企业,这从分行业的利润率上可以发现。
利用大萧条后英美产业不振的机会,日本抄底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工业能力在 30 年代也取得了很大发展,例如抄袭普拉特惠特尼黄蜂发动机的三菱“金星”,作为“日本心”出现在各种国产新锐飞机的身上,并成为三菱航空发动机系列化发展的基石,一时间日本愤青为“自主创新”军事技术的大跃进如痴如狂,痛击美帝,膺惩暴支的妄想甚嚣尘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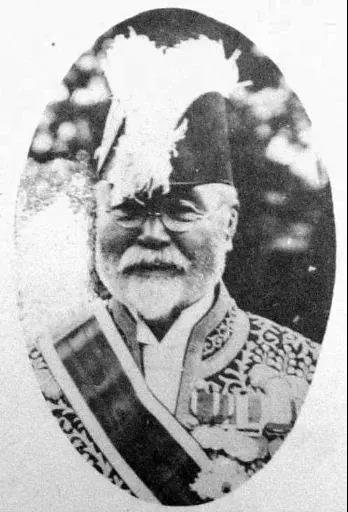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靠着一腔蛮勇之气上位的陆军少壮派军人仍然抱持着北一辉以来日本法西斯运动的总目标,即国家总动员和对中美开战。制造 918 事件的石原莞尔,一向被视为陆军唯一的战略家,他的疯狂言论颇具代表性,“欧洲大战形成的五个超级大国的世界,最终将必然归于一个体系,其统制的中心将通过西方代表美国与东方选手之日本间的争霸战而确定” “拥戴天皇的日本必须是联盟中核心性存在,从悠久的远古开始就拥有东方道义的道统的天皇是世界上唯一自然天成的王者,天皇成为东亚联盟的盟主之时,就是东亚联盟完成之日”。
法西斯势力对日本经济未来出路的规划同样是强盗逻辑的产物,一厢情愿地试图将东亚大陆作为自己的原料供应来源和商品输出市场,重建一个新的区域经济循环,若中国不接受这一安排,则断然以武力占领。“我国现在经济困难的重要原因固然是由于世界性经济萧条,但纵观欧洲战争后的趋势,与各大国经济发展相比,我国产业立国基础薄弱无疑是一个基本原因。因此为打开这一困境必须向海外发展”。石原莞尔的这一席话,概括了大陆政策的基本逻辑。
对英美工业制成品以及原油的高度依赖,注定了这种倚仗武力的贸易保护主义经济政策必然失败的命运,事实上, 1931 年冒进的大陆政策使日本与英美关系出现质变,引发英美战略遏制动作升级,而英美的遏制,反过来又强化日本国内法西斯运动的躁动,被他们视为印证其正确性与动员迫切性的证据, 918 事件爆发后,当风闻英法等国可能要对日本采取经济制裁时,帝国在乡军人会立刻印发宣传品,叫嚣道:“帝国借此机会在国内实行产业统制,彻底改变以往那种美国情况一变,多数国民立即陷入困境,一根生丝左右外交的产业结构,对出口杜绝品实行转产,获取对接壤地方的销售垄断权,积极掩有满蒙资源。果如此,则自给自足不难实现,经济封锁不足惧”。一种预期自我实现的妄想症不可救药的走向恶化。
30年代中期,日本的工业能力较之一战之初已经膨胀了6倍以上,经济发展成就在主要强国中仅次于苏联,然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已经失去可持续性的公共债务基础之上,只是依靠高桥是清的个人魅力和声望,通过超常规的货币政策维持日本金融体系的运转。
1934 年后,随着内外部经济形势好转,高桥是清试图逐步采取措施退出宽松政策,然而此时的日本政治氛围已经完全被军部总动员需要所统治。通过沸沸扬扬的“天皇机关说”事件,皇道思想占据了舆论与道德制高点。政党政治家、华族与宫廷集团养虎为患的结果,就是被这股疯狂的潮流裹挟,骑虎难下,高桥是清的努力,反而引来了陆军势力的仇视。
1936年2月26日,近卫步兵第三联队中桥基明中尉带领六十名士兵闯入高桥是清宅邸,连开七枪击毙这位老政治家,随后挥刀乱砍,甚至将高桥的内脏挑出,死状之惨,为 226 事件被难者中仅见,在天真的青年皇道派官兵眼中,高桥是清这样政党政治的化石,阻碍国家改造,实属罪大恶极,理应天诛。
226事件以皇道派暴走失败告终,陆军内部形成了统制派独大的局面,对于权柄在手的青年将校而言,国家改造运动全面实施的时机来临了,在随后的广田弘毅过渡内阁中,正式复活了海陆军大臣现役制,大正时代护宪运动的成果丧失殆尽。
日本货币体系积累的问题也一举爆发,高桥是清的后继者马场瑛一为逢迎陆海军退出伦敦裁军会议后急速膨胀的军费需求,试图搞加码版的货币宽松,结果“马场财政”一败涂地。
.jpg)


1937 年起日本再次陷入严重的国际收支危机。尽管当局颁布严格的资本管制措施,然而此时的日本经济,已经无法吸引美元借贷者的任何兴趣,这一时期日本出现了资本项目与经常项目双赤字的罕见局面,总的年均赤字额高达3亿日元,是二战前最高水平。1940 年日本官方黄金储备仅145吨,较1930年的620 吨已缩水大半。直到战败为止,日本一直是巨额的金银流出。
战前日本的经验表明,具有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后发国家在适当政策刺激下,的确可以成功摆脱贫困的恶性循环,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期,通过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的过程加速吸收发达国家经济、科技发展成果,在短时间内改变社会面貌,对于其中的“优等生”而言,国力的充实也足以支撑某种程度的地缘政治抱负,在地区国际事务中获得更大的权力。
然而出色的发展绩效同时也蕴含着巨大的危险,后发国家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的转移有其界限,而工业技术、海外市场等能够扩大经济迂回空间的因素仍十分落后,因此平均利润率下滑的铁律在这类国家经济周期末期体现得特别明显,也特别顽固,相比之下,本土资产阶级反应往往迟疑而滞后,缺乏调整经验,其路径依赖的背后是增长阶段所形成既有利益格局的强大惯性。经济泡沫化的持续时间人为拉长,直至将政策工具的腾挪空间消耗殆尽,尽管可以维持宏观指标的稳定,然而隐性危机的代价必然在微观层面得到反映,然而后发国家落后的社会结构恰恰决定了其承受经济波动的能力不足,这使对外转移危机成为最为可行的选项。
一旦挑唆民意的潘多拉魔盒被打开,随后的进程往往将超出所有当事者的控制,这类权贵资本主义裹挟的落后国家贸然用武力打破国际体系,其结局的凄惨已经被太多历史教训所证明。反讽的是,在 1945 年紧张的终战活动中,宫廷集团又一次成为主导力量奔走于幕后,一如其在 20年代培养极端派的热情,始作俑者,最终也尝到了骑虎难下的苦涩滋味。 70 年后的今天,某新兴强国似乎又有重走这一道路的充分迹象,只不过较之其山寨的日本军国主义,当下的喧嚣中更少真诚而更多投机,其冒险的前途较之日本将更为黯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