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涡中的刘慈欣
随着电影《流浪地球》的上映,中国的科幻电影开始登堂入室。然而,在成功的票房背后的是两极分化的舆论场,各种评论争吵不休。有意思的是,很多评论都是聚焦在政治立场和价值观上进行评价,却很少针对电影本身。也因为这些舆论,原作者刘慈欣站在了风口浪尖。但是,对于刘慈欣的评价(特别是对于他本人政治立场和价值观的评价)不能仅仅基于这部电影,而应该进行更细致的全面考察。

似是而非的立场
很多人看了电影后,对刘慈欣贴上了各种标签,比如法西斯主义者,小粉红,直男癌等等。然而,除刘本人公开承认过自己是科技至上主义外,很多标签都站不住脚。比如说很多人认为他支持极权主义,但刘也明白极权主义的恶果。他在对《三声》访谈者的回答中说道:“如果大灾难的时间长,比如几百年,这种极权体制,会抹杀人的创造力,而人类的创造力是人们生存最根本的力量。如果创造力都没了,短时间看没关系,长时间看,科学就没有发展、被锁死了。而科学是在大灾难面前唯一能拯救人类的东西。”(《对话刘慈欣:听起来平淡无奇,其实非常离经叛道》,邵乐乐)。在小说《三体》中他也借章北海之口说:“仅靠生存本身是不能保证生存的,发展是生存的最好保障……专制制度是人类发展的最大障碍。”
说刘慈欣是小粉红也同样站不住脚,他对中国社会的矛盾与问题十分清楚。在《三体3——死神永生》完成后记中他写道:“现在,平静已经延续了二十多年,感觉到在社会基层,有什么东西正在绷紧,压跨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随时都可能出现。”在各种公开的场合中,他并没有支持现有政权的话语出现。
在政治问题上,刘慈欣很狡猾地选择了一种不可知论的态度,他说:“政治体制我一直认为无所谓好坏,关键看它在什么地方、什么环境下……判断一个体制好坏绝不是实用主义,它是很终极的一个东西。你不能在离开它所处的环境情况下判断它的好坏,这和实用主义没有关系。甚至扩大一点,人类历史上做的任何一件事情,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离不开人类的终极目标。你先把终极目标定下来,我才能知道这个做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问题是,现在全人类研究了几千年的终极目标,没有一个确定的。所以我们现在很难对现实做出最终极的是非判断。”(《对话刘慈欣:听起来平淡无奇,其实非常离经叛道》,邵乐乐)。这是一种很典型的去政治化的态度。
刘慈欣对于科幻文学本身的态度同样也反映出这一点,他在很多访谈中表示自己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不感兴趣,而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感兴趣。他认为科幻文学最重要的东西是培养和加深人们对宇宙宏大深远的感觉,对人在宇宙的位置有更深刻的认识,对人类的终极目的有一种好奇和追求愿望(《刘慈欣访谈:道德的尽头就是科幻的开始》,《南方都市报》)。科幻是一种闲情逸致的文学,核心是很浅薄的东西,就是对科学、对未知、对宇宙的惊奇感(《夏笳、刘慈欣访谈录》)。这种态度与唯美主义提倡艺术的使命在于为人类提供感观上的愉悦十分类似。从这个意义上讲,刘慈欣的科幻观是唯美主义文学观在科幻文学领域的体现。
然而遗憾的是,虽然表面上刘慈欣表达出一种去政治化的态度,但实际上其很多科幻作品里仍然讨论了大量政治内容,用科幻的方式描写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探讨人类自身的问题,传达出自己的价值取向。甚至其作品《时间移民》《赡养人类》《镜子》等几乎是纯粹讨论政治与社会问题。当然,唯美主义本身就如此矛盾,从来不会有纯粹的为艺术而艺术,唯美主义者们在各个不同的政治立场和价值观下进行艺术创作。刘慈欣也是如此,表面上说科幻文学是提供各种可能性,实际上只提供了精英主义的可能性。要明白刘慈欣这种态度的根源,我们必须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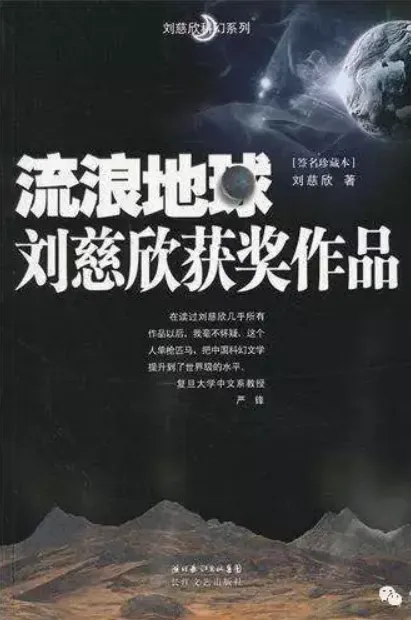
伤痕文学与十七年文学的混血儿
我们应该先知道刘慈欣的成长背景。刘慈欣的父亲为初中学历,在那个到处都是文盲的年代已经算是学历较高,从军队退伍后被分配到北京煤炭设计院工作。然而文革爆发时因为一封信被下放到山西阳泉,当了一辈子的煤矿工人,一直在井下工作。当时刘慈欣只有3岁。后来他回忆说:“阳泉是个武斗的重灾区,我依稀记得一些模糊的画面,比如有很多带枪的人一卡车一卡车地走过,夜里总有枪声,家人不让我出门……而纵观中国现代史,能让人性彻底绝望的事件,我想来想去,想不出第二个,只有‘文革’。那时候,人性最丑恶的一面都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刘慈欣:全中国能养活自己的科幻作家不超过3个》,《山西晚报》)。
这是很典型的知识精英与技术官僚在文革时期的遭遇(虽然刘慈欣父亲可能不算知识精英和技术官僚,但相同的遭遇给刘慈欣带来了知识精英和技术官僚的认同感),《三体》中叶文洁的父亲叶哲泰是这一形象极端化后的产物。
文革对当代中国人的影响是巨大的,刘慈欣也并不例外,文革塑造了刘慈欣的政治视野。从此,刘慈欣看待人类社会的态度就是知识精英与技术官僚对待文革的态度:理性的知识精英和技术官僚与不理性的幼稚愚昧的普罗大众或民粹主义政府间的斗争。《流浪地球》《地球大炮》和《三体》最明显反映了这种政治视野。《三体》中除了第一部直接描写文革的部分,在第三部中也塑造了一群幼稚的民众,他们选举出了一个低能的执剑人。然而幼稚的却是刘慈欣本人。即使按照当代的资产阶级代议民主制,执剑人也更类似于大法官这样被任命产生而不是直选产生。从中可以看出刘慈欣的社会科学知识和政治视野是极度缺乏的,甚至比不上同时代的一些自由派人士。在刘慈欣眼里,政治体制大概只有民粹和极权两种模式,至于无政府主义式左翼民粹还是法西斯式右翼民粹,资产阶级军事极权还是斯大林式官僚极权,以及其他的资产阶级代议民主制或者苏维埃民主制,都对其一无所知,极其缺乏社会科学的想象力。
当然这也是一个普遍现象。就像旷新年所说,整个80年代,中国文学都笼罩在文革的阴影下。无论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还是改革文学,都带有强烈的文革痕迹。在这之中成长的一代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最大的梦魇就是文革,最希望的事也就是文革不再重来,甚至对此达到了神经质的程度。虽然他们大部分人对文革的理解极其肤浅,聚焦在自身经历上。直到今天,都有很多自由派知识分子不断呼吁人们警惕文革重来。由于这些人很多居于体制内上层,无法完全去政治化,于是警惕文革就成了去革命化(虽然文革不是革命)。只要不发生革命,就一切能发展好(能保证我自己的生活一直好)。这种机械的进步观点当然完全是站不住脚的,它忽略了发展的内在动力问题。
刘慈欣也继承了这一套逻辑(甚至不如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看到了极权与民粹也可以相互并存,提出解决方案是实行资产阶级代议民主制)。在他的作品里,与其说大灾难是来自于自然与宇宙,不如说是来自于文革式的动乱。在与江晓原的对话中也提到,如果大灾难发生时,可以用一种芯片控制人的思想,把人更好地组织起来对付灾难(《为什么人类还值得拯救?——刘慈欣 VS 江晓原》)。从这一点来说,刘慈欣是伤痕文学的后裔,是典型的80年代保守主义知识精英的精神气质(这里所指伤痕文学也包括反思文学,当前文艺学普遍将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分开,但两者并无本质区别)。
然而文革不仅仅是对知识分子和技术官僚造成伤害,它对普通民众的伤害更大。迈斯纳总结文革对中国人的精神影响时说:“运动没有实现其声称的目标,留下的只是溃散后对政治冷漠的人民,冷漠之后是虚无,一个厌倦了的民族冷眼旁观1970年代发生在上层的拜占庭式的政治斗争和宫廷阴谋……一个逐渐玩世不恭、对政治冷漠的民族,已很难再为陈旧的革命口号和思想说教所打动。”(《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如果说文革之后上层只是去革命化,那么普通群众就完全去政治化了。刘慈欣就是这样一种去政治化,这造成了其文学观上的唯美主义。
但和上层知识分子不同,普通工人虽然去政治化,对于毛时代仍然会有一种情怀(上层知识分子在新体制下是受益者,对毛时代并无多少怀念,也因此和十七年文学划清了界线)。刘慈欣虽然在央企工作,但并没有进入中国社会的上层,反而一直呆在基层,这也使得他具有一种普通工人的视角。这种情怀具有多种原因,不过最后都会用一种浪漫化的笔调来叙述毛时代与苏联时代。比如在《球状闪电》中刘慈欣写道:“汽车驶进了科学城,两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建筑在雪雾中掠过,有一次,我肯定看到了一尊列宁的塑像。这是一个让人产生怀旧感的城市,那些有上千年历史的古城并不能使人产生这种感情,它们太旧了,旧得与你没有关系,旧得让人失去了感觉。但像这样年轻的城市,却使你想起一个刚刚逝去的时代,在那个时代你度过了童年和少年,那是你自己的上古时代,你自己的公元前。”甚至会有一种共产主义情结,《赡养人类》是典型代表。《全频带阻塞干扰》和《球状闪电》里也描写了俄罗斯经济私有化后的灾难,《乡村教师》和《中国太阳》底层情结的表现也很明显。当然,共产主义在这里仅仅是情怀,不是一种意识形态,与苏联红色科幻完全不同,但是却神奇地具有了十七年文学(指1949年到1966年的文学)的影子。
当然,伤痕文学与十七年文学也有很多内在一致之处,比如说往往都有对新社会的乐观展望(虽然是虚幻的乐观),对个人前途的肯定和对官僚集团(至少是对其中一部分)的信任等。这些特质也被刘慈欣所继承(虚幻的乐观最后走向了伪乐观)。
这种混合使得刘慈欣成为了一个独特的存在,成为伤痕文学和十七年文学的混血儿。而这种特质,也为今天的刘慈欣热打下了基础。这也说明了所谓的去政治化根本就不可能存在。

右翼的宏大叙事
刘慈欣热是近几年的现象,在这之前他只是在科幻迷的小圈子里面比较活跃。而他现在的走红,官方以及自干五群体是背后重要的推手之一。那么,为什么官方和自干五群体会选择刘慈欣?
这需要在中国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里找答案。在改革开放之后,原有的毛主义一套说辞早已陈腐不堪,除了一小部分毛派,无论是社会精英还是普通群众都对其深恶痛绝。但新的意识形态建立却困难重重。既不能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那意味着要落实巴黎公社式民主,摧毁官僚集团),又不能用自由主义的观点(那意味着否定自身政权合法性),面临着左右为难的情况。邓提出的“不争论”实际上也是为了将建立新意识形态的问题暂时搁置。后来虽然搞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但更像是纸糊的墙壁,完全无法发挥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功能。这一问题一直搁置到现在。
这种情况下,五花八门的各种社会意识都进入了人民的脑海。气功、法X功等先后在社会上横行一时,发挥着主旋律无法发挥的作用。相比社会底层各阶级,资产阶级和官僚集团的精神危机似乎更加严重。要不然沐浴在欧风美雨里,对自家情况不闻不问或者冷嘲热讽,买办性明显;要不然纸醉金迷,沉迷在吃喝嫖赌等感官刺激中,难以承担大国统治者的责任。这和中国飞速发展的经济形成了鲜明对比。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民族资本集团逐渐形成。这一群体的产生,必然要求形成中国特色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一方面要保证符合现实,另一方面也要保证政权的历史合法性。而能贯穿整个新中国历史的,就只有工业化的进程和掌握政权的官僚集团。除此之外几乎没有未发生改变的事物了。因此,新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塑造只能从这两个事物入手进行,其他的都会面临自相矛盾的结果。这种意识形态的产物就是工业党(虽然这也是个缺乏根基的空洞意识形态,号召力很有限,只是比主旋律好点)。
《那年那兔那些事》和《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就是这种工业党民族主义的典型代表作品。其以歌颂中国发展的巨大成就和官僚集团保家卫国的丰功伟绩为主。同时其表达方式也借鉴了日本右翼艺术作品煽情式的套路,这比国内主旋律作品要高明许多,也是其获得成功的原因之一。
刘慈欣显然要更加高明,其优秀的科幻写作能力本身在科幻文学界就已是一方诸侯,比起周小平花千芳之流显然要高出几个层次。虽然其作品没有直接正面歌颂中国工业化成就和官僚集团功绩,但其价值核心是一致的,强调科技进步和知识精英的作用(这样的科幻作品在当代已经不多,很多当代科幻作品都是对人类未来悲观绝望且反对科学主义的),同时对新中国历史有一定情怀。作为伤痕文学和十七年文学的混血儿,刘慈欣显然有资格成为新时代工业党民族主义的代表(虽然刘慈欣本人并没有有意识成为这种意识形态的代表,再次说明了去政治化的不可行性)。
刘慈欣之所以受自干五的追捧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其作品里的伪英雄主义。纵观其作品,很多都是一个主题,那就是“生存”,讲在极端环境下人或者文明如何生存下去。他在回答《三联周刊》的问题时也说:“关于我的世界观(只是科幻的世界观),她说的也许对(‘世界终究要毁灭,但在毁灭之前,我们要好好燃烧一次’),但燃烧是为了继续生存,在我的小说中希望总是存在的,更多关注的是,在极端的境遇到来之际,文明为了生存下去,如何摆脱道德的羁绊。”(《三联周刊关于目前科幻状况的的采访》)。那么文明如何生存下去?刘慈欣回答说:“当太阳系驶入一片星际尘埃中,恶化的地球生态必须让三十亿人去死以防止六十亿人一起死,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文学是否还要继续嘲笑英雄主义呢?那时高喊人性和人权能救人类吗?从科幻的角度看人类,我们的种族是极其脆弱的,在这冷酷的宇宙中,人类必须勇敢地牺牲其中的一部分以换取整个文明的持续,这就需要英雄主义了。”(《从大海见一滴水》)。
刘慈欣理直气壮地喊出了“英雄主义”的口号。只不过吊诡的是,真正的英雄主义意味着自我牺牲与保护他人,而刘慈欣式的伪英雄主义是牺牲别人与保全自己。虽然在《吞食者》与《全频带阻塞干扰》里塑造了一种自我牺牲的真正的英雄主义,但这显然不是刘慈欣自己的思想。刘慈欣在与江晓原的辩论中有一个著名的吃人理论,他说:“做个思想实验。假如人类世界只剩你我她了,我们三个携带着人类文明的一切。而咱俩必须吃了她才能生存下去,你吃吗?”(《为什么人类还值得拯救?——刘慈欣 VS 江晓原》)刘慈欣的选择是吃人,但是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主动被吃。试想一下,如果选择主动被吃,那么这种最崇高的道德恰恰最有利于文明生存。他这种观念也延续到了《三体》中,将牺牲他人换取自己生存的褚岩作为英雄的代表之一。这种伪英雄主义将文明与道德对立起来,根本没想过道德是延续文明的保障之一。如果没有追求自由与人权的自我牺牲,没有真正英雄主义的道德,人类能不能生存到现在还是个未知数,这是最为崇高的道德与人性。
这种伪英雄主义之所以盛行,其实也是后文革时代的特征之一。文革用崇高的革命口号将群众运动起来,却又干着利己的勾当。文革之后的中国人已经变得政治冷漠,玩世不恭,不相信任何理想主义与崇高道德,只剩下精致的利己主义。
同时,这种伪英雄主义也与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弥漫在全世界的绝望情绪遥相呼应。江晓原说:“刘慈欣虽然持有强烈的科学主义信念,他的《三体》却并没有科学主义纲领之下应有的乐观主义。通常,科学主义信念一定会向读者许诺一个美好的未来……纵观刘慈欣的一系列小说作品,正如他的粉丝们怀着复杂的心情所发现的那样,刘慈欣对未来是越来越悲观了。《三体》更走向了大悲极致——人类文明被轻而易举地毁灭了。”(《百年科幻:中国与西方接轨,刘慈欣却反潮流》)。这与当代科幻主流的悲观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处,所不同的是当代科幻主流是赤裸裸的悲观,而刘慈欣仍然有一种伪乐观。
处于晚期资本主义时代却又在资本主义上升期的中国,是一个进步又衰落的矛盾体,夹杂着君临天下的喜悦和行将就木的恐惧。既没有希望,又不能绝望。伪英雄主义提供了这样一种矛盾情绪的寄托。与世界上其他地方彻底绝望的右翼比起来,中国的右翼仍然捧着虚假的希望。
而推崇这种伪英雄主义的自干五,对应着自干五们本身极低的行动力。和当年日本右翼相比,今天的中国右翼更少的真诚与更多的投机,也光明正大地支持着投机主义。

跛足的史诗与科幻的未来
《科幻世界》副主编姚海军说:“刘慈欣用旺盛的精力建成了一个光年尺度上的展览馆,里面藏满了宇宙文明史中科学与技术创造出来的超越常人想象的神迹。进入刘慈欣的世界,你立刻会感受到如粒子风暴般扑面而来的澎湃的激情——对科学,对技术的激情。正是这种激情,使他的世界灿烂银河之心。这激情不仅体现在他建构宏大场景的行为上,也体现在他笔下人物的命运抉择中。那些被宏大世界反衬得孤独而弱小的生命的这种抉择从另一个角度给人震撼,增加了作品的厚重感。”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严峰说:“刘慈欣的世界,涵盖了从奇点到宇宙边际的所有尺度,跨越了从白垩纪到未来千年的漫长时光,其思想的速度和广度,早已超越了‘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 的传统境界。但是刘慈欣的意义,远不限于想象的宏大瑰丽。在飞翔和超越之际,刘慈欣从来没有停止关注现实问题,人类的困境和人性的极限。”不错,刘慈欣的作品像一部宇宙史诗,能让读者领略到壮丽且空灵的宇宙之美和科学技术近乎神迹般的力量。他对自然科学规律和物质技术的理解加上非凡的想象力使得他能构建出一个雄伟辽阔的世界。如果其作品都能像《思想者》和《微观尽头》等作品一样纯粹探讨宇宙之美和科学规律(按照刘慈欣自己的说法,这是他进行科幻创作第一个阶段:纯科幻阶段,《刘慈欣:重返伊甸园——科幻创作十年回顾》),那么刘慈欣毫无疑问会是公认的优秀科幻作家。
不过刘慈欣显然并不是这样,正如很多评论人和前面本文所说的,他是在用科幻的方式关注人类现实问题,这一点刘慈欣本人也承认。刘慈欣对自己的科幻创作阶段有过回顾:“从思维方式上,我的科幻创作大概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纯科幻阶段。第二阶段:人与自然的阶段。第三阶段:社会实验阶段。”(《刘慈欣:重返伊甸园——科幻创作十年回顾》)。刘慈欣说自己最后支持的是第二种创作方式,他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科幻永恒的主题。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也是最困难的创作方式,因为这需要对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双重把握,是第一种方式和第三种方式的结合体。很明显,刘慈欣最好的作品还停留在第一种创作方式上。
正如本文前面所提到的,由于他对社会科学的极端无知和贫乏的想象力使得其对人类的关注极其空洞。刘慈欣承认过自己小说的缺点:“不光是我,以前的很多科幻小说都存在这个问题,其中的人物都很单薄,人物就是个可有可无的符号……与主流文学相比,科幻小说在人物塑造和描写上肯定没法比,很多科幻小说的描写对象并不是在人物身上,而是在环境身上,比如说将一个星球环境和一个种族作为一个文学对象来描写,作为科幻小说的一个优势,往往对人物的注意力要小些。当然有人物描写更好。”(《刘慈欣访谈:道德的尽头就是科幻的开始》,《南方都市报》)。刘慈欣指出了自己对人物的塑造很单薄这个问题,却忽略了另外一个更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对人类社会运动规律的忽视,缺乏社会科学的想象力。如果没有对社会运动规律的把握,那么描写的人类整体也极度空虚乏味。刘慈欣的作品是史诗,但却是跛足的史诗,一边是波澜壮阔的宇宙,另一边却是简单空洞的人类社会。
刘慈欣说,我们都是阴沟里的虫子,但总得有人仰望星空。不过他只仰望了一半的星空,对人类社会这片星空视而不见。其实,对人类社会进步的推动恰恰是让人类摆脱阴沟的途径,能让人类更好地仰望星空。并且人类社会同样是一片星空,是一片不亚于自然世界的星空。社会运行规律的美感也不会亚于自然科学规律。促使人类社会进步的运动既是现实,又是未来;既是当下发生的事,又是一个遥远的愿景。如果科幻文学一直忽略掉社会科学,那么永远是跛足的和难以前进的文学。
实际上科幻文学的确是在衰落中。刘慈欣说:“早在2013年,美国科幻界就有过一场关于科幻文学是否走向衰竭的大讨论……美国科幻现在处于一种恶性循环中:新一代的青少年读者在流失,科幻读者平均年龄越来越大。而读者老化会更进一步强调作品的文学性,不再重视激情和创新。”(《夏笳、刘慈欣访谈录》)。中国同样也是如此,刘慈欣说:“中国仅有两个科幻杂志,其中一个就在山西,它的名字叫《科幻大王》。但很戏剧性的是,就在媒体聚焦科幻,科幻大热的今天,这家办了将近20年的杂志社在不久前悄悄地死亡、倒闭了。”(《刘慈欣:全中国能养活自己的科幻作家不超过3个》,《山西晚报》)。刘慈欣热并没有带动中国科幻的发展,甚至他自己除了《三体》等少部分作品外,其他作品同样没有受到太多关注。这也说明了当前的刘慈欣热只是出于政治因素,而不是科幻文学因素。科幻作家飞氘曾经形容中国科幻是一支“寂寞的伏兵”,一小群人在很少有人能注意到的荒原里默默练兵,在某些合适的时机会杀出几员猛将,来一个精彩的亮相,引发一片喝彩,但之后还是一样无人问津。
这是很正常的现象,正如刘慈欣所说,科幻的骨子里是天真,“这里的天真是一种信念,一种思维方式:坚信人类可以了解宇宙,通过科学可以创造出种种奇迹,开拓美好的未来;坚信人在宇宙中可以生存下去,可以看到宇宙中最精彩的奥秘,能航行到宇宙的边界。”(《刘慈欣:科幻不应把科学技术妖魔化》,《中国青年报》)。也就是说,只有在一个处于发展上升期的社会,人们对于未来的生活充满希望,坚信发展的前途光明无限的环境下,科幻文学才能得到较大发展。最早期的科幻是这样,19世纪是科幻的古典主义时代,凡尔纳是代表人物,那时也是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上升年代。苏俄早期的宇宙主义科幻浪潮是对古典主义科幻的继承,洋溢着乐观与希望。中国1980年代的科幻热也继承了这一特点。这些都是那种乐观主义社会背景下的产物。
在当代,科幻的主流是反科学主义,江晓原说:“一个多世纪以来,几乎所有西方科幻作品中的未来世界,都是黑暗和荒谬的……西方科幻作品以反思科学技术为己任,作品中普遍展示科学技术过度发展的荒谬后果,反复警示科学狂人滥用科学技术对社会的祸害,不断警告资本借助科学技术疯狂逐利最终将极度危害地球环境和公众的安全。”(《百年科幻:中国与西方接轨,刘慈欣却反潮流》)。这非常符合现代西方资本主义下的情景:科技在资本的控制下已经不再是进步的工具,而是反动的工具。但是,大部分的西方科幻作家并没有因此转向支持新社会制度的建立,而是把批判矛头指向了科技本身,或者仅仅只是批判资本而不号召推翻资本统治。这样的结果只能是通向一个黑暗荒谬且野蛮的世界,就像罗莎·卢森堡所说,要么社会主义,要么野蛮主义。如果不选择社会主义,那么就必然走向野蛮主义,现代西方科幻作品很遗憾地走向了野蛮主义。其实不光是科幻文学,主流文学同样如此。当代的主流文学,特别是后现代文学,其压抑、彷徨、焦虑和无助感让读者心情异常沉重。它们都是晚期资本主义下的精神产物。
实际上刘慈欣早期具有真正的乐观主义精神,他说:“从社会使命来说,科幻不应是一块冰冷的石头,无情地打碎人类的所有梦想,而应是一支火炬,在寒冷的远方给人以希望;从文学角度讲,真正的美景最终还是要从光明和希望中得到。把美好的未来展示给人们,是科幻文学所独有的功能。”(《理想之路——科幻和理想社会》)。(《微纪元》是刘慈欣不可多得的乐观主义作品,可惜也并没有对于其社会运行的详细描写,仍然是一部跛足的史诗。)不过这种乐观主义只是毛时代话语体系的情怀和遗产,而非真正的革命精神。它不符合中国现实,随着时间必然会渐渐消逝,走向悲观。
无论是科幻文学还是主流文学,都建立在产生它们的社会土壤上。就像马克思所说:“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成为希腊人的幻想的基础、从而成为希腊‘艺术’的基础的那种对自然的观点和对社会关系的观点,能够同走锭精纺机、铁道、机车和电报并存吗?在罗伯茨公司面前,武尔坎又在哪里?在避雷针面前,丘比特又在哪里?在动产信用公司面前,海尔梅斯又在哪里?”(《<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文学需要土壤,在客观上文学的边界受着同时代社会科学的边界制约,文学是在人类社会形态及其日常生活模式上运用各种方式所传达的内容,它往往不会超越同时代社会科学自身的想象力(玄幻等文学形式除外)。
科幻文学比主流文学还要多一层边界,那就是自然科学的边界。刘慈欣说:“前沿理论科学家在科学想象力上确实远高于科幻小说家,事实上,科幻小说是依赖于他们的想象力才存在的,科幻小说中最超远的想象,也很少越出这些科学如来佛的掌心……科幻小说的任务之一,就是把科学家的想象以文学方式展示给大众。”(《三联周刊关于目前科幻状况的的采访》)。刘慈欣看到了自然科学的边界,但他没有看到社会科学的边界,这导致了他科幻中一个重要因素的缺失。同样,这反过来也证明了好的科幻文学比好的主流文学往往要更加难得。
必须承认的是,当代社会科学主流中,对未来社会制度的想象力也同样缺乏,很难绕开资本主义谈其他社会制度。但激进的社会科学也同样存在。他们让人民知道,社会主义不是幻想,而是一个“真实的乌托邦”(赖特语)。如果没有一个民主的,自由的,充分尊重人性的,消灭阶级压迫的,不按市场规律运行的,消除人的异化的社会主义社会,那么不止是科幻文学,现存的许多文化艺术都要随着资本主义进入野蛮时代而消失。
文学(尤其是科幻文学)如果不能和建立新社会的运动联系起来,那么就只能转向悲观绝望。当然,这种革命的、真正英雄主义的文学并不是塑造出假大空的人物形象和无聊乏味的理想国(那是斯大林式官僚最爱干的事,他们将其命名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也是十七年文学的特征,提供一种虚幻的乐观),而是用一种真正乐观主义的精神深刻细致地描写新社会的种种可能的困难和问题,成为新时代艺术的建设者。
十月革命后,托洛茨基展望新时代文学时说:“社会的漩涡还不会很快静息下来。在欧美还将有数十年的斗争。不仅我们这一代人,而且还有下一代人,都将成为斗争的参加者、英雄和殉难者。这一时代的艺术将整个地带有革命的标志。这种艺术需要新的意识。这一意识首先是与公开的或伪装为浪漫情调的神秘主义不相容的,因为革命的出发点是这样一个中心思想:集体的人应当成为唯一的主人,他的力量的大小取决于他认识和利用各种自然力量的本领。这一意识与悲观主义、怀疑主义及所有其他种类的精神沮丧也是不相容的。它是现实主义的,积极的,充满着能动的集体主义和相信未来的无限的创造信念……”(《文学与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