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尔斯是个社会主义者?
奎斯奇(Ed Quish) 著
陈宗延 译
宋治德 校
译按:本文为美国左翼期刊《雅各宾》(Jacobin)关于美国法哲学学者威廉·A·埃德蒙逊(William A. Edmundson)最新著作《罗尔斯:缄默的社会主义者》(John Rawls: Reticent Socialist)之书评。
关于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伦理学家罗尔斯(John Rawls,1921-2002)思想与左翼思潮或甚至马克思思想的比较,是一个历久不衰的争论问题。过去一般都将两者视为殊异甚至对立起来的说法为主导。在英语世界的政治哲学理论领域,一直有种声音是试图将罗尔斯的理论(尤其是正义观)与左翼或马克思主义之间进行互补对话,而且近十多年来更为明显。威廉·A·埃德蒙逊去年出版的这本新书,就是其中的一个突出例子,认为罗尔斯晚年已经走向社会主义。然而,本文作者奎斯奇对于威廉·A·埃德蒙逊此著作亦提出了他的不足之处和批评。
:约翰‧罗尔斯像。原文引自Encyclopedia-Britannica。-1.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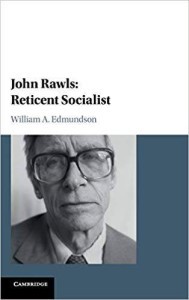
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以二十世纪卓越的自由派哲学家为人所纪念。但他到生命的尽头时,对资本主义却持锐利的批判。
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是二十世纪卓越的自由派哲学家之一。他的主要著作《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1971年)重新定义了政治哲学的领域,形塑其后几个世代的政治学、伦理学、法律的学术研究。对许多仰慕者来说,罗尔斯代表了最出色的自由主义传统,而他的正义论为自由主义最人道的希望提出了严谨的辩护:一个既保留又抑制资本主义的民主福利国家。
对左派批评者而言,罗尔斯的理论对不正义的批判往往看似不足。由罗尔斯著名的思想实验推导得出的正义社会——理性的各方在“原初状态”(original position)中设计出一套社会契约,而不知道他们在自己创造出的社会中的最终地位(译按:因为“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的作用)——大体上反映了美国的基本社会、政治和法律的制度。罗尔斯的基本理论取径冒着巩固既有秩序的风险,使之看似共识思路(consensual reasoning)为无可避免的产物——模糊而非阐明了政治的可能性。
在《约翰·罗尔斯:缄默的社会主义者》(John Rawls: Reticent Socialist)一书,威廉·A·埃德蒙逊(William A. Edmundson)聚焦于罗尔斯最成熟且激进的著作,借此由左派立场为这位哲学家辩护。当罗尔斯名为《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Justice as Fairness: A Restatement,译按:或作《正义即公平》)的最后著作于2001年出版时,他总结:资本主义无法与正义所需的政治平等和公平机会兼容。罗尔斯想象两类超越资本主义而可能同等地实现正义的政体:“自由民主社会主义”(liberal democratic socialism)及他所谓的“拥有财产权的民主”(property-owning democracy)。埃德蒙逊认为,罗尔斯对此宣称的中立立场具有误导性,而他成熟的理论实则系统性地偏好于社会主义。假使考虑到罗尔斯拒绝搬出社会主义的基本论点,可将罗尔斯视为一位“缄默的社会主义者”。
埃德蒙逊本人无论就他对社会主义的支持或对罗尔斯的赞扬而论,则并不缄默。他将他的民主—社会主义政治(democratic-socialist politics)概念,直截了当地定位在罗尔斯自由民主理论(liberal democracy)的界域之内,声称:比起其它盛行的理论框架,“罗尔斯的理论更能够提供一种共同语言,使充分心系正义而想理解它、实现它的人们能够相互沟通。”
埃德蒙逊提出了有力的例子,认为“社会主义宪政主义”(socialist constitutionalism)值得在当代左翼论辩中占有一席之地。然而罗尔斯的缄默不仅仅是埃德蒙逊所愿意承认的这些——且突出了罗尔斯在有关社会主义政治的政治哲学概念的局限。
正义即公平
罗尔斯并未追求在《正义论》中止息任何当下的政治论辩。他的野心更为深沉。他希望借由发展一套同时诉诸基本道德直觉以及理性自利的正义论,道德理论能促进一种公共的“正义感”(sense of justice),这种正义感将分裂性的冲突置于商定(agreed-upon)原则的脉络中。若我们能够同意“正义”意味着什么,我们对于政治和经济的冲突的看法或许至少能够立基于共同的基础上。与其各说各话,我们或许能聚焦于我们都共同心系的某些事:生活在一个正义的社会意味着甚么。
罗尔斯解释他的理论(他称之为“正义即公平”)的方式,是将之与效用主义(utilitarianism,社会应保障“为最多数人的善的最大化”之观点)对比。他如此推理:效用主义作为一种权利的理论和对公共善的解释,是有所不足的。在效用主义下,总是诉诸善的最大化以取代基本的权利和自由,而平均效用最大化对最劣势的人所受的未置一词;即使总体效用提升了,他们却可能迎来更糟的后果。
这些顾虑激发了罗尔斯正义论的两个原则:
1) 每个人对于平等的基本自由最广泛的、而又与所有人的自由之类似体系兼容的整个体系,都有一种平等的权利。
2) 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安排应能,使它们(a)对最少受益者有最大的利益……以及(b) 在公平的机会均等的条件下,所依系的职位和职务要向所有人开放。
第一个原则所保护的基本自由,包含选举权和出任公职的权利;言论、集会和良心的自由权;免受任意逮捕和拘押的保障;以及“拥有(个人)财产的权利”。第二个原则则在这些权利受到保障后规范分配;而既然没有任何公民可从任其基本需求未被满足的制度安排中获益,许多人主张它暗示着社会最低保障。
由于罗尔斯想要引导而非止息争议的论辩,他的理论给社会主义留下一扇敞开的门。他思索:某种具有自由—民主制度的“市场社会主义”(market socialism)(他说,而非一党制、苏维埃式的体系)能够实现“正义即公平”。
他的基本原则,看起来仍然暗暗偏好资本主义。把握第一个原则优先于第二个原则,罗尔斯将“个人”财产的权利置于分配性的要求之上。尽管他主张这个优先级兼容于平等主义的财产和机会分配,他很清楚表明形成社会契约的基础必须是个体权利,而非共善。相对于社会主义希望的共享丰裕,他的第二个原则诉诸经济成长为“水涨船高”(the rising tide that lifts all boats)的形象,暗示了若不平等可以改善最劣势者的前景则具有正当性。(校按: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科恩(G.A.Cohen)提出“正当性社群”(justificatory community)的观念,亦对此有所批评,见他的《诱因、不平等和社群》(Incentives, Inequality, and Community)文章, 收录在G.B.Peterson所编于1992出版的The Tanner Lectures on Human Values: XIII。)
当罗尔斯论及他的理论可能造成的经济结果时,他也花费了更多时间讨论它如何适用于“一个准许私人占有资本和自然资源的、经过适当组织的民主国家”。倘若税赋、移转给付(transfers)和公共益品维持机会均等且巩固政治民主,资本主义可能是正义的。
“正义即公平”或许与社会主义眉来眼去,但不难看出为何许多人将之视为对福利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辩护。
重思资本主义
当罗尔斯撰写《正义论》时,即在民权运动的立法成就之后、战后婴儿潮的尾声之际,他对于自由民主正在一条基本上正义、平等的路径上前进这件事感到希望十足。然而时至1990年代中期,他忧心自由民主正在衰微。埃德蒙逊引用罗尔斯以前一位学生,哲学家乔舒亚·科恩(Joshua Cohen)的话:“[罗尔斯的]希望之感被世界摇撼了。他的感觉已然变灰”(译按:引自Roger, Ben. (1999). Portrait: John Rawls. Prospect, June 1999, 55.一文)
当其它自由主义者庆祝历史的终结时,罗尔斯烦恼于私人选举资金如何使得有组织的富人支配了政治过程。政治自由——例如竞选公职、使用言论和集会自由影响立法、以及在公平的选举中投票——或许在形式上授与了所有的人,但若是富人的权力取代了普通民众在决定政治结果方面的权力,这些权利便不是对所有公民都有着“公平价值”(fair value)。在埃德蒙逊的叙述中,确保所有公民的政治自由的公平价值这件必要之事,是驱使罗尔斯迈向社会主义的核心议题。
罗尔斯在《正义新论》中强调他的一般理论中一项长期的面向,现今被称为其“起组织作用的核心理念”(central organizing idea):社会作为一个社会合作的公平体系(society as a fair system of social cooperation)的想法。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将社会视为“就像所有人全都同意购买而期待赢得奖品的一场游戏或彩票”。(译按:语出Friedman, M. (1962). Capitalism and Freedo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中译版《资本主义与自由》,商务印书馆,2004。),罗尔斯则将社会视为一场合作的努力,应当有利于每一个人。对罗尔斯来说,社会合作是与正义的法律秩序并行而运作,它本身是由一个所有公民都有公平机会影响的民主国家所支撑。但若是富人支配政治体系,结果是阶级支配而非人民主权──从属于命令,而非依照规则合作。
几十年前,罗尔斯曾认为福利国家资本主义能够逼近他理想的正义社会。在里根革命(Reagan Revolution)造成的破坏之后,他得出的结论认为它是不可能的。
在他的成熟著作中,罗尔斯主张福利国家资本主义的核心瑕疵在于它“准许一个由很少人组成的阶级来垄断生产资料”。这种控制使少数人能够“制定一个法律和财产的体系,不仅确保他们在政治上的支配位置,也确保他们在经济中的支配位置”(译按:语出Rawls, J. (2008). 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S. Freeman Ed.).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中译版《政治哲学史讲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尽管福利国家资本主义的重分配许诺暗示了对机会均等的“某种程度的关切”,但它准许权力集中而侵蚀民主的这一事实不仅意味着它无力保护政治自由:它“否认政治自由的公平价值”。
埃德蒙逊主张,在罗尔斯生涯之末,他是个社会主义者。
“自由民主社会主义”与“拥有财产权的民主”
罗尔斯仍留下了暧昧的空间。在《正义新论》中,他写道“自由民主社会主义”和“拥有财产权的民主”二者皆可能实现正义。埃德蒙逊的书花了诸多篇幅,环绕在澄清罗尔斯原本如何可能更全面地评估在这两种政体间而做的选择。
它们的基本区别,集中在它们的宪政会允许何种类型的所有权(这是非常特定的区别,因为它们共享了重大的相似性)。对两种情况,目标都是保障政治权利和均等机会的公平价值——不准许形成特权阶级,将经济权力转化为政治支配。两者也都维护政治权利和法治(rule of law)、鼓励健全的公共领域、并确保公平的选举。
在社会主义的情况下,主要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能够保障所有公民成为资产的共同所有者是一项宪政权利,而这些资产是公民成为社会的合作成员所需的。在埃德蒙逊的叙述中,这些资料包含了银行业和金融、交通、通讯、保险以及某些主要产业(但他并未阐明清楚这个范畴的具体边界)。埃德蒙逊如此写道:“关键的想法是这样:生产资料是那些若未被每一个人所共同拥有,则会如人们熟知地那般,使他们陷入拥有者与非所有者、收租者与交租者的支配与从属的关系中的资本资产”。至于在自由社会主义政体的“制高点”(commanding heights)之下会发生甚么就比较不清楚了,尽管罗尔斯和埃德蒙逊都认为工人所有的公司之间存在市场竞争。
那么“拥有财产权的民主”又如何?就罗尔斯的观点,工人所有的公司和公有制也都有可能存在于拥有财产权的民主中,但与社会主义不同的是,拥有财产权的民主“准许”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罗尔斯仍旧将拥有财产权的民主视为资本主义的一项替代方案——资本主义是“立基于”私有制,拥有财产权的民主则仅仅在主要资本能够被普遍分配的情况下,才“准许”主要资本的私有。与广泛的公有制和去商品化形成对比,拥有财产权的民主强调“各种各样的教育和培训”、“为所有人提供的基本的健康照护标准”、使用税收限制世代内部和世代间的不平等、以及确保“生产性资产广泛所有”的反垄断条款。
由于罗尔斯并未排除在民主社会主义的制高点之下拥有财产权的民主或私有制具社会主义元素,埃德蒙逊主张我们必须将上述的区别画出一条非常清楚的界线:亦即主要生产资料是否始终应该被选定为私有制的载体,还是我们应当在宪政上禁止生产资料的私有化。社会主义的选项会承认,民主不兼容于私人公民从每个人要成为社会的合作成员所需的主要资产中占有及榨取租金。
这项区分有助于埃德蒙逊的论述,并让他找出偏好公有制的有力的罗尔斯式理由:例如,重要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意味着传达互惠性,以及对比我们每个人是否获得足够份额的争论不休而更能促进稳定性。但借由将这些选项分类成不同的宪政“政体”,埃德蒙逊将重要的实务论辩转置于高级法(higher law)的领域。他聚焦于高级法,不仅将“制高点”下发生什么事这种棘手的问题搁置一边,却也造成了一种风险,即把社会主义变成一种宪政论辩之事,而非一个实际斗争的领域。
要处理在民主社会主义和拥有财产权的民主之间作选择所引起的问题,与其运用宪政理论,似乎更需要罗尔斯时常称之为“政治社会学”(political sociology)的东西:何时能为了正义和民主的缘故而驯服市场,而何时它们必须被取代?哪些资产是我们需要集体的人民控制,以扭转自由民主朝向阶级支配的倾向?而或许更重要的是,何种政治战略和集体行动能带来基进的社会变革?
宪政的路障
埃德蒙逊将焦点放在宪政作为政治斗争的场所是正确的,但他或许并未将关于宪政的争论放在正确的战略界域(strategic parameters)中。
在美国宪法之下,保护资本家的权利限缩了工人的民主权利且抑制了平等的自由。生产资料在宪政上(大多)被视为私人资产而受保护,任何社会化都服从于“征收条款”(takings clause)(译按:见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该条款要求补偿私有者,使他们即刻成为有力的债权人。最后,由于最高法院的竞选经费法理论(campaign finance jurisprudence),使到要确保罗尔斯意义下民主自由的公平价值几乎变成不合法了,因为限制竞选支出被视为对自由言论的潜在威胁,而须服从于违宪审查(judicial review)。
即使在宪政之外,保护资本家的权利超过工人也是政治预设,无论在平常或不平常的政治时刻都未受质疑。举一个突出的例子,金融危机创造了一个将主要金融机构拱上公共领域的机会,借由将金融变成可民主课责的公共权力的一环来终结“大到不能倒”(too-big to fail)的谬论。然而奥巴马却选择资本主义超过民主,他说:“我们想要留住私人资本强大的用处(strong sense),以满足这个国家的核心投资需求”。如埃德蒙逊所述,“其实不止于此:在资本主义体系中,那种‘强大的用处’并不仅仅根植于权宜之便(expediency),而是在于台面下的、私人资本家的基本个体权利”。
我们应当如何与不民主的宪政斗争?埃德蒙逊诉诸于“在宪政上筑壕守卫(entrench)生产资料”,而这只可能紧跟着转化性的社会变革而来。而尽管埃德蒙逊绝非盲目无视政治意志的问题,他对于引人注目的宪政改革纲领该如何实行却很少关注。
再一次地,我们或许会说,集体行动和政治策略超出了罗尔斯理论及埃德蒙逊对其重新构连(re-articulation)的范围。政治哲学驻足于宪政论述的高级法中,而其它人才设法解决手段的问题。但正如市场作为一种商品交换形式的范围及意义,有关培力集体行动的问题也应该位在社会主义哲学的核心。往坏处想,罗尔斯和埃德蒙逊偏好的宪政主义焦点,造成的风险是使集体手段与目标分离,并使政治行动从属于特定且有限的施动者:律师、知识分子和政治家。
这些工具并非本质上就引人不快,且可能对任何真正的社会主义进展来说都是必须的。但社会主义政治哲学的核心必须要培力工人和受压迫者。为此,社会主义需要其人民权利的保卫者(tribunes of the people)甚于需要其法学家。
罗尔斯的缄默
倘若罗尔斯真是一位社会主义者,为何它如此缄默?
埃德蒙逊最具说服力的答案,根源自罗尔斯的多元主义概念。罗尔斯希望它的正义论能有助于商定社会多元主义,他将多元主义理解为不同的人们具有不同的道德世界观的倾向,并将之视为多样的现代社会的基本事实。对许多社会主义来说,社会主义不仅是一套正义宪政体制的理论,且是罗尔斯所谓的“统合性学说”(comprehensive doctrine):一种社会进步的道德视野——人类学习直立行走。
罗尔斯对这种类型的社会主义从不感到自在,因为它造成了一种风险,即国家权力与公民宗教结合起来而将后者强制加诸于多元社会。对罗尔斯来说,任何看似可行的社会主义,都必须要从自由主义传统如何商定宗教多元主义学习,且需要坚决避免国家和意识型态间的这种联系。
不过罗尔斯的缄默或者也衍生自他从黑格尔身上学到的另外一课。在《正义新论》中,罗尔斯主张哲学的目标之一是调和我们与我们的世界——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当我们合理地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反过来这个世界看起来就是合理的”(译按:语出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对罗尔斯来说,这不仅意味着接受我们的制度如何合理地发展,更是鼓励我们“积极地接受和认可我们的社会世界,而不是仅仅听命于它”。同样的句子,给予马克思批判空想社会主义的灵感。要改变世界,我们不能仅仅抽象地想象一个更好的未来,而需要把握我们社会中的矛盾如何创造解放的机会。
如实接受世界是行动的先决条件,但认可则钝化了这个我们之中多数人无法共享我们创造的丰裕世界所造成的不正义经验。倘若罗尔斯的缄默以过于自信的“统合性学说”的形式阻隔了一种意识型态,那么它却保留了另一种形式的意识型态:我们自己的世俗祭司(our own secular priests)的意识形态。
2018年8月22日
原载于《雅各宾杂志》(Jacobin Magazine)
本文为《约翰·罗尔斯:缄默的社会主义者》(John Rawls: Reticent Socialist)(剑桥大学出版社,2017年,见下图右)之书评。本文作者奎斯奇(Ed Quish)为康乃尔大学政治理论博士生。
原文题目:John Rawls, Socialist?
原文链接:
https://jacobinmag.com/2018/08/john-rawls-reticent-socialist-review-theory-of-just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