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劣等性的神话
目录
艾芙琳·瑞德 著
雷奥 译
五叶 校
性别不平等是资本主义社会及通常而言的阶级社会的显著特点。男性是经济、文化、政治和智识生活中的主人,而女性则扮演从属甚至是服从的角色。仅在近几年,女性才渐渐从厨房与育儿室中走出来,挑战男性的垄断地位。但是本质上的不平等依然存在。
从几千年前阶级社会伊始时,性别不平等就已经成为了它的标志,并且贯穿了它的三个主要阶段:动产奴隶制(chattel slavery),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由于这个原因,男性统治恰如其分地被描述为阶级社会的特点。服务男性利益的私有财产制度、国家、教会和家庭模式都在支撑与维系男性的统治。
由于这样的历史状况,关于男性的社会优越性的某些错误言论得以普及,男性之所以在社会中具有优越性,是因为他们天生就具有优越性,这种说法被当成是亘古不变的公理。这种说法把男性特权视为一种自然法则,而非社会历史特定阶段的某种社会现象。据说男性天生就拥有更优越的身体素质与精神品质。
一种有关女性的荒诞说法也不胫而走,为上述说法提供了支持。女性在社会中的劣势地位是因为她们天生就具有劣势,这种说法同样被视为亘古不变的公理。它的依据是什么呢?女性都是母亲!据说是大自然规定了女性的社会劣势。
这是对自然史与社会历史的歪曲。贬低女性而抬高男性的,是阶级社会而非大自然。男性在对女性的斗争与征服中赢得了他们在社会的优势地位。不过,这种性别斗争只是巨大的社会斗争(原始社会的覆灭及阶级社会的建立)的一小部分。造成女性劣等性的社会制度,同样也造成并巩固了其它形式的数不尽的不公正、劣等、歧视与屈辱。但是,说女性天生就比男性劣等的神话,却将社会史的这个过程掩盖了。
是阶级社会而非大自然,剥夺了女性行使社会高级职能的权利,并且强调女性的动物性生育功能。一种双重的神话贯穿于剥削女性权利的历史过程中。一方面,母亲身份代表了由于女性的生殖器官造成的一种生理折磨。除了这种庸俗的唯物主义,母亲身份还被认为代表了某些近乎神秘的东西。为了安抚作为二等公民的女性,母亲被说成是神圣的,被赋予了光环,拥有天赋的特殊“本能”,以及具备男性永远无法理解的感情与知识。在阶级社会统治下,女性受到的社会性剥夺本是一种屈辱,却被说成是神圣的。
但是,阶级社会并非亘古长存,它只有几千年的历史。男性并非始终是占优势地位的性别,因为他们并非始终是生产、智力与文化领域的领导者。恰恰相反,在原始社会中,女性并未被神化,也未遭到侮辱,女性是社会上与文化上的领导者。
原始社会是母系制度。顾名思义,母系制由女性而非男性担任领导者与组织者。但是,母权制与父权制的区别,不仅是领导角色方面的性别逆转。在原始社会中,女性的领导权不是建立在对男性的剥夺上。相反,人们并未发现原始社会有任何形式的社会不平等、劣等或歧视的现象。原始社会是完全平等的。事实上,男性是在女性的领导下,才得以超脱较为落后的禀赋,上升为更高级的社会与文化角色。
在早期的母系社会,生育能力不被视为一种折磨或劣等性的象征,而被认为是大自然的伟大馈赠。母亲身份赋予了女性权力与声望,而这是很有理由的。
人类产生于动物界。大自然只将生育的器官与机能赋予雌性。正如罗伯特·布里福特(Robert Briffault)在他的著作《母亲》[①]中详细论证过的,这种生物禀赋架起了通往人性的自然桥梁。正是雌性承担了喂养、照顾与保护幼崽的关怀与责任。
然而,正如马克思与恩格斯已经论证过的,古往今来所有类型的社会都是以劳动为基础的。因此,不仅是女人的生育能力发挥了决定性影响(因为所有的雌性动物都会生育)。对于人类这个物种而言,关键在于是生育是劳动的存在前提。生育与劳动的结合,使得首个人类社会制度得以建立。
是母亲这个群体,开辟了人类的劳动之路,因而也打开了通往人性的道路。母亲一度是主要的生产者:工匠和农民,也是科学、智力与文化生活的领导者。这恰恰由于她们是母亲,而且生育与劳动在最初的时候就已经结合在一起了。在原始人类的语言中,能够发现这种结合的痕迹:“母亲”一词,意指“生产者—生育者”。
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女性是天生的优等性别。每一种性别都脱胎于自然进化,都有着它特殊且不可替代的角色。然而,如果我们硬要用“社会领导权”这一衡量当今男性的标准来评价过去的女性,那么我们必须承认早在男性取得领导权的很久以前,女性早就是社会的领导者了,并且这一地位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本篇报告的目的是要一劳永逸地粉碎阶级社会传播的神话:女性天生就是劣等的。反驳这种神话的最有效方式,首要的便是展示原始社会女性的劳动史料。
.png)
对食物供给的控制
获得食物对任何一个社会来说都是最引人注目的问题,因为只有吃饱后人们更高级形式的劳动才成为可能。鉴于动物每天都得觅食才能活下去,如果人类想要前进和发展,就必须取得一些控制其食物供给的措施。控制不仅意味着为今天准备充足的食物,而且还有多余的可以留给明天,并且还有能力为未来的使用保留储备。
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类历史可以被分为两个主要时期:持续了几十万年的食物采集时期;以及食物生产时期,起源于农耕和畜牧的发明,不早于8000—10000年以前。
在食物采集时期最初的劳动分工是非常简单的。它通常被描述为一种性别分工,或者在女性和男性间的劳动分工。(孩子们在他们足够成熟后就会贡献出他们的份额,女孩们在女性职业方面受到训练,男孩们则在男性职业上。)这种劳动分工的本质是不同性别在采食的方法和种类上的区别。男性是大猎物的狩猎者——一种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使他们离开家庭或者营地的全职工作。女性则是营地或者居住地周围蔬菜作物的收集者。
如今必须明白的是,除了在特定历史时期世界上几个特别的地区外,最可靠的食物供给来源不是动物(由男性提供)而是蔬菜(由女性提供)。正如欧提斯·塔夫顿·梅森(Otis Tufton Mason)写道:
“无论人类部落曾经到过何处,女性都已经找出能作为他们主要依赖的伟大的主要产品。在玻利尼西亚它是稗子,或者面包果;在非洲它是棕榈和木薯,粟米或者山药;在亚洲它是大米;在欧洲它是谷物;在美洲它是玉米和土豆,或在某些地方它是橡子和鸟的翅膀。[②]
亚历山大·戈登韦泽(Alexander Goldenweiser)持有同样的观点:
“无论什么地方,在家庭的食物供应方面,由居家女性的劳动提供的食物与她们那些游猎者丈夫和儿子所提供的东西相比要更为规律和可靠。事实上,在所有原始部族中的一个常见现象就是:男性,结束一次或多或少费力的追猎返家时,可能空手而归而他自己还需要食物。在这样的情况下,家庭的蔬菜供应既要满足男性所需还要满足家庭的其他成员。”[③]
因此最可靠的食物供给是由女性收集者提供的,而不是男性猎手。
但女性也是猎手——慢猎物和小型猎物的猎手。除了挖掘根、茎、植物等,她们还收集幼虫、昆虫、蜥蜴、软体动物和其他小型动物例如野兔、有袋动物等。女性的这类活动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大部分这种小型猎物都曾被活着带回营地,而这些动物为动物的驯化和家养提供了第一手经验和实验的基础。
因此关于动物驯养的至关重要的技术都始于女性之手,这些技术最终在畜牧业中发展到顶峰。而这种驯化在母性方面有根源。在这一点上,梅森写道:
“最初的驯养纯粹就是对无助的幼崽的收养。幼崽或者小羊羔或者小牛犊被打猎手带回家。它受到母亲和她的孩子们的喂养和照料,甚至被用她自己的乳房喂养。难以计数的参考资料能支持母亲对野生生物的囚禁和驯化……女性总是特别和家养动物中产奶产毛的物种联系在一起。[④]
一方面女性的食物采集活动由此带来了动物驯养的重大发现,同时在另一方面引领了农业的发现。使用挖掘棒——人类最早的工具之一——来挖取地里的食物是女性的劳动。直到今天,在世界上的一些落后地区,这种挖掘棒对于女性来说依然和她的孩子一样是她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例如,当内华达州和怀俄明州的肖松尼族印第安人被发现时,她们被白人称为“挖掘者”,因为她们依然使用这项技术来获得食物。
正是因为通过这种棍棒挖掘活动,女性才最终发现了农业。詹姆斯·弗雷泽爵士(Sir James Frazer)对该过程的最初阶段做了一种很好的阐述。用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地区中部的原住民作为例子,他写道:
“她们用于掘根的工具是一根7—8英尺长,在火中硬化并且末端削尖的杆,这种杆也用作进攻和防身的武器。在这里我们也许可以发现一些她们从挖掘进步到系统化耕作所经过的步骤。
“长棒子被牢牢地插入地面,它被摇动以用来松土,而土被左手指铲起又抛出,这样她们挖得飞快。但劳动量与收获量之比,很大。为了得到一个周长大约半英尺的山药,她们必须挖一个大约1平方英尺,2英尺深的大坑。因而这项工作就占用了女性和孩子们相当可观的一部分时间。
“在山药大量生长的肥沃地区,土地会坑洞遍布;简直就是在上面打孔。掘土寻找根和山药使土壤变得更加肥沃,由此可以增加根茎植物和草本植物的产量。在被挖掘棒翻掘过的土地上簸扬种子自然会造成相同的结果。可以肯定的是,簸扬种子——风吹走其中一些种子——会结出果实。[⑤]

久而久之,女性学会了通过清除园圃中的杂草和保护正在生长的植物来帮助大自然。最后,她们学会怎么播种然后等待它们生长。对此,A·S·戴蒙德(A. S. Dimond)写道:
“一些食物采集者发现,例如,山药的冠部——在为了食用而去掉其块茎部分后——放回土中还能够再次生长。这项技术一旦在某种植物或根茎或谷物上被习得之后,就能延伸到别的植物、根茎、谷物上去。在栽培的过程中,不仅仅数量得到保证,而且质量也开始提高。”[⑥]
不仅数量和质量得到提高,而且一整系列的植物和蔬菜的新品种都会被培育出来。依据查普尔和库恩(Chapple & Coon)所述:
“通过栽培,选择的过程已经生产出许多新品种或者深刻地改变了老品种的特征。美拉尼西亚的人们种出的山药有6英尺长1英尺甚至更厚。澳大利亚人从野地里挖来的可怜的根还不如一根雪茄粗。”[⑦]
梅森如下总结了农业发展所经历的步骤:
“原始农业首先经过找寻蔬菜,接近它们,给它们除掉杂草,播撒种子,用手培育它们,最后是家畜的使用。”[⑧]
据戈登·柴尔德(Gordon Childe)所说,每一种比较重要的食用植物,以及其他植物例如亚麻、棉花,都是在前文明时期由女性发现的。[⑨]
农业的发现和动物的驯化使得人类超过食物采集时期而进入食物生产时期变为可能,并且这种组合代表着人类对其食物供应的首次征服。这项征服是由女性完成的。给畜生和男性提供了食物的伟大的农业革命,是女性使用挖掘棒的劳动取得的最高成就。
然而,为了获得对食物供给的控制,意味着不能仅仅依靠大自然和它的肥力。它尤其需要的是女性对自己的劳动、学习以及创新和发明的能力的依靠。女性不得不找出适合各品种植物或者谷物的特定培育方法。她们必须掌握打谷、簸谷、磨谷等技术,并且发明出所有用来犁地、收割、储存庄稼,然后将其转化为食物的特殊工具和其他必要器具来。
换句话说,为了赢得对食物供给的控制而进行的斗争,不仅导致了农业的发展,而且导致了制造和科学的最初要领的发现。正如梅森写道:
“女性的整个生产生活曾是围绕着食物供给建立起来的。从获取原材料的第一次徒步旅行到食物被盛好和吃掉,其中有一系列手艺都是连续的,并且是自然的产物。”[⑩]
生产、科学和医学中的女性
性别间的第一次劳动分工经常被以一种简化而误导性的公式描述出来。它声称,男性是猎手和战士;女性则待在营地或是居屋中,抚养孩子,做饭和其他所有的事情。这种描述引起了一种见解,即原始家庭只不过是现代家庭的一种更为原始的副本。当男性正在提供所有社会必需品时,女性仅仅在厨房和婴儿房附近闲逛。这样的观念是对事实的一种严重歪曲。
除了在食物获取上的区别,两性在所有高级形式的生产领域里实际上并没有劳动的分工,原因很简单:原始社会的整个生产生活牢牢地掌控于女性手中。例如,(那时的)烹饪并不是我们熟知的现代个体家庭的模样。烹饪仅仅是一种女性作为发现和控制火、对受控热源的掌握的结果而获得的一项技术。
对火的使用
自然界中的所有动物都惧怕火并逃离它。然而对火的发现可追溯到至少五十万年前,在人类完全成为人类之前。关于这一重大征服,戈登·查尔德写道:
“对于火的掌握,是人对一种强大的物理力量和一种显著的化学变化的控制。在历史上第一次,一个自然的造物指挥着自然的伟大力量之一。这种对力量的运用必然对控制者发生反作用……在增强和减弱火焰、传播和使用它的过程中,人类与其他动物的行为发生了革命性的偏离。他是在声明自己的人性和创造自己。”[⑪]
所有伴随火的发现而来的基础烹饪技巧——烧、煮、烤、烘、蒸等——都是由女性发展起来的。这些技术涉及了一种对火和受控热源的特性的不断实验。正是在这个实验中,妇女发展了为将来的使用而保存和储藏食物的技术。通过火和热的应用,妇女把肉类和蔬菜烘干并保存起来以供未来之需。
但火代表的东西要更多得多:火是原始社会工具之王;它可以等于在现代社会中对电或甚至原子能的控制和使用。而正是女性——她们开发了所有的早期产业——发现了火在其生产中的用途。
女性的最初生产生活围绕着食物供给。准备,保存和保护食物需要发明所有必要的附属设备:容器,炊具,烤炉,储藏室等。女性是第一个隐藏所、粮仓和食品仓库的建造者。其中一些粮仓是她们在地上挖的并用稻草衬里。在潮湿、沼泽的地面上,她们在高于地面的杆上建起了仓库。保护粮仓中的食物免受害虫的需要导致了另一种动物——猫的驯化。梅森写道:
“对于发明粮仓和保护粮食免受害虫破坏的角色,世界必须感谢女性对猫的驯养……为了保护粮仓,妇女驯服了野猫。”[⑫]
同样还是女性,分离出了食物中有毒和有害的物质。在这个过程中,她们经常使用受控热源将自然状态下不可食用的东西转化为一种新的食物供给。再次引用梅森:
“有许多地方的植物在自然状态下是有毒的或极端刺激或刺鼻。在这些土地上生活的女性都独立地发现,煮沸或加热可驱除(植物中)有毒或令人不适的元素。”[⑬]
例如,木薯在其自然状态下是有毒的。但是,女性通过一个复杂的过程将这种植物转化为一种主要的食物供给,这种过程是在一个篮子压榨机中挤出其有毒内容,并通过加热将其残留物排出。
许多不可食用的植物和物质被女性在生产过程中得到利用,或转化为药品。丹尼尔·麦克肯泽博士(Dr. Dan McKenzie)列出了数以百计由原始女性通过她们与植物的亲密接触而发现的顺势疗法。其中一些仍在被照旧使用;其他的只是略有改进。其中就有因其麻醉性质而被利用的重要物质。[⑭]
妇女发现了,例如松焦油和松脂的特性;以及大风子油的特性,它如今被当作治疗麻风病的药物。她们从刺槐、酒精、杏仁、阿魏、香脂、蒌叶、咖啡因、樟脑、香菜、洋地黄、树胶、大麦水、薰衣草、亚麻籽、欧芹、胡椒、石榴、罂粟、大黄、远志草、蔗糖、苦艾,以及数百种其他物质中发明了各种顺势治疗药。根据这些天然物质的发现位置,这些发明来自南美洲、非洲、北美、中国、欧洲、埃及等。
妇女将动物性物质和植物性物质转化为治疗药。例如,她们将蛇毒转化为一种用于抵抗蛇咬伤的血清(今天由蛇毒制备的等效制剂被称为“蛇毒抗毒血清”)。
在与食品供给有关的生产活动中,需要各种类型的容器来装载,运输,烹饪和储存食物,以及用于盛放食品和饮料。根据自然环境,这些容器是由木材,树皮,兽皮,褶皱纤维,皮革等制成。最终,女性发现了用粘土做罐的技术。
火被用作制造木制容器的一项工具。梅森给出了对这种技术的描述;并且可以容易地理解相同的技术是如何被扩展到第一艘独木舟和其他航海器的制造的:
“通过对火的不断仔细检查和控制,她们烧出了空心的部分。然后,这些神奇的万事通去了火,并用草做的临时扫帚扫除了碎渣。她用自己制作的燧石刮刀挖出木炭,直到一块干净的木材表面露出来。重复烧制和刮除直到容器变成所需的样子。槽完成后,只要肉备好,石头烧热,它就做好了为全家烹煮的准备。[⑮]
在这种显著的转化中,木材,这种通常会被火吞噬的物质,被制成用于在火上烹调食物的容器。
由争取控制食物供给的斗争而产生的女性的生产活动很快就超过了这一有限范围。当一个需求得到满足时,新的需求就出现了,而这些需求又会在新需求和新产品的上升的螺旋中得到满足。正是在这种新需求以及新产品的产生中,女性为将来的更高级文化奠定了基础。
科学与女性的生产活动并行产生。戈登·柴尔德指出,将面粉转化为面包需要一系列相关的发明,以及有关生物化学和微生物、酵母的使用的知识。制造面包的生物化学知识同样也制造了第一批发酵酒。柴尔德声称,制罐的化学、纺纱的物理学、织机的机械学和亚麻和棉花的植物学也必须归功于妇女。
从绳索到织物
绳索看起来或许是一种非常不起眼的工艺品,但是绳子的编织仅仅是一整条产业链的开始,而这条产业链以大型纺织工业为结尾。甚至绳子的制造需要的不仅仅是手工技能,还要有挑选、处理、操作所用材料的知识。查布和库恩写道:
“所有已知的人种都使用绳索,无论它是用于捆绑工具手柄,制作兔子网和绳袋,或在他们的脖子上系上饰物。在兽皮最常被使用的地方,如爱斯基摩人中,绳子可能主要由从兽皮和动物肌腱上切下来的条组成;很少使用兽皮且生活在森林中的人则使用植物纤维,例如藤,木槿,纤维和云杉根,这些东西不需要二次处理便可用。其他纤维是短的,必须绞合在一起成为连续的绳或线。”[⑯]
从编织技术产生出了篮子制造业。根据所在地不同,这些篮子由树皮、草、树韧皮、兽皮、根制成。一些是编织的,其他类型的是缝制的。篮子和其他编织品的种类繁多。罗伯特·洛伊(Robert H. Lowie)列出了其中一些:承重篮、水瓶、浅碗、干酪盘、盾牌(在刚果)、帽子和摇篮(在加利福尼亚州)、风扇、背包、垫子、盒子、鱼篓等。其中一些篮子的编织之紧密,以至于它们已经不透水了,可用于烹饪和存储。[⑰]
布里福特写道,其中一些的做工非常精美以致现代机械也不能复制:
“原始妇女编织的树皮和草纤维经常是如此的神奇,甚至有机器之资源的今人也无法模仿。所谓的巴拿马帽子——当中最好的可以压扁后穿过一枚戒指——就是一个为人熟知的例子。[⑱]
在这个行业,妇女利用任何她们可获得的自然资源。在有椰子的地区,一种出众的绳索是用椰子皮的纤维制成的。在菲律宾,一种不可食用的香蕉品种给著名的马尼拉麻提供编织材料。在波利尼西亚,构树因其树皮而被栽培;树皮经妇女锤打后,被制成布,她们再用这块布给男人和女人做衬衫、袋、皮带等。
纺织工业随着伟大的农业革命而出现。在这个复杂的工业中,妇女将在农业和工业中学到的技术融合在一起。正如戈登·柴尔德写道:
“纺织工业不仅需要对亚麻,棉花和羊毛等特殊物质的知识,而且还需要特殊动物的繁殖和特定植物的种植。”[⑲]
此外,纺织工业需要高度的机械化和技术技能,以及整个系列的附带发明。这样的行业要想发展,查尔德继续道,
“……需要另一个复杂的发现和发明,一个更为先进的科学知识体系必须得到实际运用……在作为前提的各种发明中,纺纱设备的发明是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织机。
“现在织机是一台非常复杂的机器——复杂得无以言表。它的使用也并不简单。织机的发明是人类智慧的伟大胜利之一。它的发明者是无名的,但他们对人类知识的财富量做出了重要贡献。”[⑳]
狩猎,除了它在增加粮食供给方面的价值外,是人类发展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在有组织的狩猎中,男人不得不与其他男人合作,这是动物世界所不知的特点,那里竞争性斗争是才规则。关于这一点,查布和库恩写道:
“打猎是对身体和大脑很好的锻炼。它刺激并可能‘选择’了自我控制、合作、受控的攻击性、机敏和创造性,以及高度的手部灵活的特质。人类在其形成时期不可能经历比这更好的学校了。[21]
制革者
然而,由于狩猎是男人的工作,历史学家很容易对它过誉。虽然男人们确实通过狩猎为食物供给做出了贡献,然而却是女人们的手准备和保存了食物,并将动物的附产品运用到他们的生产中。是女性发明了鞣制和保存兽皮的技术,并创立了伟大的制革业。
制革是一种漫长、困难和复杂的过程。洛伊描述了这种劳动的最早期形式,它仍然为火地岛的奥纳女性所沿用。他告诉我们,当猎人带回了一张蜥蜴皮,那里的女性
“……跪在僵硬的生皮上,用石英刀片用力地刮去脂肪组织和下面的透明层。过了一会儿,她用拳头揉捏皮片,一遍遍揉捏整个表面,并常常用上她的牙齿,直到兽皮软化为止。如果要去掉毛发,也用同一把刮刀完成。[22]
洛伊所说的刮刀是人类最古老的两种工具之一,另一种是挖掘棒。与蔬菜采集和随后农业中使用的木制挖掘棒一起,演变出了制造业用的碎石、刮刀,或“拳斧”。关于这一点,布里福特写道:
“构成了史前工具一个极大部分的‘刮刀’是由女性所使用和制造的……关于这些刮刀的可能用途也有很多争议。最能使怀疑主义缄默的事实是,爱斯基摩女性在当今使用的器具与那些她们的欧洲姐妹在冰河时代的漂流砾石(drift gravels)中大量留下的器具相同。
“爱斯基摩女性的刮刀和刀子通常被精心地甚至艺术般地安装在木制手柄上。在南非,这个国家遍布与旧石器时代的欧洲相同的刮刀。从与布什曼人密切相识的人的证词中得知,这些工具是由女性制造的。[23]
梅森证实了这一点:
“刮刀是世界上的所有工艺中最古老的一种。蒙大拿的印第安女性仍然从她们的母亲那里得到她们的手艺,而母亲的手艺又是由她们的母亲传授的——一个从人类诞生以来就不间断的继承。”[24]
鞣制
但是,像大多数其他手艺一样,制革需要的不仅仅是体力劳动。女性在这门手艺中也必须学习化学的秘密,并且在她们的劳动过程中,她们学会了使用一种物质来造成另一种物质的转变。
鞣制本质上就是一种生皮的化学变化。洛伊写道,在爱斯基摩人中,这种化学变化是通过在一池尿液中浸泡兽皮来实现的。在北美,印第安女性在特殊的药剂中使用动物的脑,兽皮被浸泡其中来实现化学变化。然而,真正的鞣制需要使用橡树皮或一些含有丹宁酸的其它植物物质。作为皮革制作过程的一部分,女性用肩抗的火把熏制皮革。北美印第安人的盾牌是如此坚硬,不仅能防箭,有时甚至可以防弹。
皮革制品和篮类制品一样广泛。洛伊列出了皮革的一些用途:亚洲游牧民将其用于瓶子;东非人用于盾牌和服装;在北美印第安人中,它被用于长袍、衬衫、连衣裙、绑腿、鹿皮鞋。后者还把皮革用于他们的帐篷、摇篮和盾牌。他们将吸烟装备和杂物存放在鹿皮袋中,并将肉保存在生皮箱中。北美原住民制造的各色精美的皮革制品、印第安女性从来没有停止带给光临收藏有她们作品的博物馆的参观者以惊喜。
布里福特指出,女性必须提前知道他们准备的特定皮革的性质,由此提前决定它最适合的产品类型:
“根据皮革的不同用途可以进行无限的变化;柔软的兽皮弄平至均匀的厚度并保持毛发所附着的层;帐篷、盾牌、独木舟、靴子所需的硬皮;用来制服装可洗涤的薄、软皮革。所有这些都需要原始的女性推敲过的特殊的技术过程。[25]
梅森写道:
“光是在美洲大陆,穿兽皮的女性就知道如何处理和利用猫、狼、狐狸、各种臭鼬、熊、浣熊、海豹、海象、水牛、麝牛、山羊、绵羊、羚羊、鹿、麋鹿、海狸、野兔、负鼠、麝鼠、鳄鱼、乌龟、鸟类和无数的鱼类和爬行动物的皮。
“经调查发现,凡是天上、地下,或水中任一有皮的东西,野蛮人女性都已经给它取过了名字,并已经成功把它变为了其充当人类衣着的原始用途,而且已经发明了其原先拥有者从未梦想过的新用途。[26]
制陶者和艺术家
制陶业,不像其他女性的生产活动,它需要自然中并不现存的全新物质的创造。关于这一点戈登?柴尔德写道:
“制陶也许是人类最早有意识使用的化学变化。其本质是她可以将一块黏土塑造成她想要的任意形状,并通过“烧制”赋予该形状持久性(即,加热到高于600摄氏度)。对于早期的人们来说,这种物质的质变一定看起来像是某种魔法变化——化泥灰为石头……
“陶器制造术的发现主要在于找出如何控制并利用刚刚提到的化学变化。但是,如同所有其他发现一样,它的实际应用包括其他方面。为了能使黏土成型,你必须让它湿润,但如果你把潮湿的塑器直接放到火中,它会破裂。在器皿能被烤制之前,加在黏土中用以塑形的水中,必须先在阳光下或者火边慢慢地干透。再一次,黏土必须经过挑选和预处理……必须设计一些清洗工序来去除粗糙物质。
“在烧制过程中,黏土不仅会改变它的物理稳定性,也会改变它的颜色。人类必须学会控制诸如此类的改变,并利用它们来增加器皿的美观性……
“因此,即使是最粗糙、最普通形状的陶制品,也已经很复杂了。它涉及到对大量独特工序的理解、对一整群发现的应用……制造陶器是人类创造性的一个有力实证。”[27]
的确,原始女性,作为第一批制陶人,捧起大地上的泥土,并用由黏土塑造了一个劳动产品的新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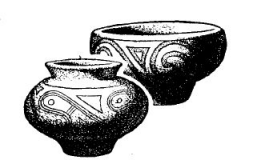
在女性的手中,装饰艺术与所有这些产业并肩发展。艺术源于劳动。正如洛伊所写:
“一个篮子制造者无意中成了一个装饰者,但是一旦这种图案吸引了人们的眼睛,它们就会被有意寻求。篮子卷纹可能让人想起旋涡在缠绕着扭索饰等等。此外,一旦这些几何图形被当作装饰物而掌握时,它们就不再需要被限制在它诞生的器物上了。制陶者可以在他的花瓶上画一个斜纹设计,雕刻师可以在他的木制高脚杯上模仿这种设计。[28]
女性的皮革产品不仅因为其功能性,而且还因为它们的装饰之美而备受赞誉。当女性到达制衣的阶段时,她们把精细的设计织入布料中,并发明了染料和染色技术。
建筑师与工程师
也许原始妇女最不不为人知的活动是她们在建造、建筑和工程上的工作。布里福特写道:
“我们不再习惯于认为建造的艺术和建筑学与制鞋或制陶一样是女性的职业了。然而,澳大利亚人、安达曼岛人、巴塔哥尼亚人、博托克多人的棚屋;塞里人的粗糙庇护所,美州印第安人的兽皮屋和圆锥屋,贝都因人的黑色驼毛帐篷,中亚游牧人的圆顶帐篷,都是女性的独家作品和特殊照顾项目。
“有时这些或多或少可移动的住宅是非常精致的。例如,“圆顶帐篷”有时是一个宽敞的房子,在几根柱的框架上建起来,斜搭成圆形,并用木制格架加固,整个覆盖上厚厚的毡,形成一个穹顶结构。内部被分为几个隔间。除了木材,所有的组成部分都是忙于建造与组装各个部件的土库曼女性的产品。
“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的‘普韦布洛人’让人想起一种东方城镇的如画图景; 层层叠叠的房子群落如阶梯般次第排列着,一个房子的平顶成为上面房子的露台。由梯子或外面的楼梯通往上层,墙壁是装饰性的锯齿形城垛……庭院和广场、街道,以及用作俱乐部和寺庙的稀奇的公共建筑……他们数不清的废墟的正是如此证明。[29]
在普韦布洛印第安人中定居的西班牙牧师对这些女性为他们建造的教堂和修道院的美丽感到震惊。他们回信给他们的欧洲同胞说:
“没有一个男人曾参与房屋的建造……这些建筑物完全由妇女、女孩和布道团中的年轻男性建立起来;因为对于这些人来说,妇女建造房子是他们的习俗。[30]
在传教士的影响下,男性开始分担这项劳动,但他们的首次尝试却遭到了自己人的讥笑。正如一位西班牙牧师写道:
“这位尴尬的可怜人被一群妇女和儿童嘲弄者包围,她们嘲讽和大笑着,认为这是她们看到过最可笑的事情——男人竟然参与了房屋的建造!”[31]
今天,恰恰是对面遭到嘲笑——女人竟然从事建筑和工程行业!
在女性的背上
女性不仅是原始社会的熟练工人。她们也是货物和设备的搬运工和干燥工。在家畜免除了女性的部分负担前,原始的运输是在她们的背上实现的。她们不仅运送了生产中使用的原材料,还将整个家庭的货物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
每一次迁徙时——这些都是在定居的村庄生活发展出来之前经常发生的——是女性拆掉帐篷、棚屋或小屋,再把它们重新搭建起来。是女性把这些重物,和她们的孩子一起,从一个定居点或营地运到另一个。而在日常生活中,是女性来运输木柴、水、食物和其他必需品的重负。
即使今天,火地岛的奥纳部落的女性,如查普尔和库恩指出,当他们改变扎营点时,她们携带的负重超过100磅。关于东非的阿肯库由人(Akikuyus),劳特利奇夫妇(Routledges)写道,男人不能举起超过40至60磅的重物,而女性则搬运100磅甚至更多:
“当一个男人说:‘这东西太重了,它只适合女人来搬,而不是男人’时,他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32]
关于女性工作的这一方面,梅森写道:
“从女性的后背到汽车和宏伟的船只(的发展),是所有艺术中最伟大的艺术的历史,它首次让人类出去探索和面对整个地球……我并不为船木工在船首雕刻一个女性头像,或是用‘她’来称呼火车头而感到奇怪。”[33]
根据我们的现代观念,是否所有这些广泛的劳动活动意味着妇女受到压迫、剥削和碾压?一点也不。事实上恰恰相反。在这一点上,布里福特写道:
“认为女性在野蛮社会中受到压迫的臆想出来的观点,部分是由于文明的男性的自满,部分是由于那些女性看上去工作非常努力。每当女性被看到从事辛苦劳动,她们就被认为处于奴隶和被压迫地位。这真是无比深的误解……
“原始女性之所以是独立的,离不开她的劳动。一般来说,正是在那些女性劳动最辛苦的社会中,她们的地位最独立、影响力最大;在她们无所事事、工作由奴隶完成的地方,通常,女性地位只比性奴稍强一点儿……
“在原始社会中,没有哪种劳动是非自愿的,并且没有哪种劳动是女性出于对专制秩序的服从而从事的。”
“谈及祖鲁妇女,一个传教士写道:‘凡是观察过这些女性在她们工作和劳动时的幸福表情、她们的欢乐和唠叨、她们的笑声和歌曲的人……都会让他把这些与我们自己劳动中的女性的举止作一番比较’”[34]
这不是劳动,而是剥削和强迫劳动,这是对人类的羞辱。
当女性开始她们的劳动时,并不曾有人教她们。她们必须通过自己的勇气和不懈努力来艰难地学习一切。她们大概从自然本身获得了一些最初的提示。梅森写道:
“女性曾受到蜘蛛、建巢者、食物储藏者和粘土中的劳作者(例如土蜂和白蚁)的指导。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生物建立了学校来教导迟钝的女人如何工作,而是意味着她们聪明的头脑时刻留意着来自这些源头提示……正是出于对勤劳的尊崇,女性才一直不懈且很好地承担了她的那部分。在人类时代的开端,她规定了自己的职责,并且她不曾松懈地履行了它们。[35]
第一个集体
但是,由于女性最初的劳动形式如此简单,许多历史学家将女性的生产活动仅仅称为“家庭工艺”或“手工艺”。事实上,在机器开发之前,除了手工艺没有其他工艺。在城镇和城市发展出专业化工厂之前,除了“家庭”并不存在其他工厂。没有这些家庭和它们的手工艺,中世纪的大行会就不可能产生。甚至整个机械化农场和流水线工业的现代世界也不可能产生。
当女性开始她们的劳动时,她们就把人类拉出了动物王国。她们是劳动的发起者和工业的创始人——是将人类从猿类状态中解脱出来的原动力。并且与她们的劳动并行出现了语言。正如恩格斯指出:
“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社会成员更紧密地互相结合起来,因为它使互相帮助和共同协作的场合增多了,并且使每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共同协作的好处……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这是唯一正确的解释……首先是劳动,在其之后与它并行的是音节清晰的语言。”[36]
虽然男性无疑由于有组织狩猎的关系而发展了一些语言,但语言的决定性发展是产生于女性的劳动活动的。正如梅森写道:
“头脑中时刻思考着各种各样生产技艺女性,一定也同样发明和固定了语言。布林顿博士在一封私人信件中说,在大多数早期的语言中,不仅有一系列的表达属于女性,而且在许多不同的地方,我们发现一种属于女性的语言是大大区别于属于男性的语言的。
“野蛮男性在狩猎和钓鱼时往往独自一人,而且必须安静,因此造成了他们的沉默不语。但是女性在一起吃饭,并且一整天都在交谈。除了文化的中心,女性仍然是最好的字典、谈话者和写信者。[37]
劳动和语言所代表的,首先最重要的是,人类集体的诞生。由于自然法则,动物必须保持彼此之间的个体竞争。但是,通过劳动,女性撤掉了自然的关系,并建立了新的、劳动集体的人类的关系。
“家庭”社区
原始的“家庭”就是整个社区。社会集体主义而非个人主义是其存在模式。在这一方面,戈登·柴尔德写道:
“新石器时代的手工艺被描绘为家庭产业。然而,工艺传统不是个人的,而是集体的传统。所有社区的成员的经验和智慧被不断汇集起来……它被父母通过榜样和说教传给孩子。帮她的母亲做壶的女儿,仔细观察她,模仿她,并且接受其口头指导、警告和建议。新石器时代的应用科学是通过我们所称的学徒制度进行传承的……
“在一个现代的非洲村庄,家庭主妇不会为了制作和烧制她的罐子而隐蔽起来。村里的所有妇女一起工作、聊天和比较笔记;她们甚至互相帮助。职业是公共的,它的规则是社区经验的结果……而新石器时代的整个经济离不开合作努力。”[38]
因此,女性劳动的最高成就是建立和巩固了第一个伟大的人类集体。用集体生活和劳动取代动物个人主义时,她们在人类社会和动物王国之间放置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她们赢得了人类的第一次伟大的征服——动物的人性化和社会化。
正是通过这项伟大的工作,女性成为第一代工人和农民;第一代科学家、医生、建筑师、工程师;第一代教师和教育家、护士、艺术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和文化遗产的传播者。她们管理的家庭不只是集体厨房和缝纫室;她们也是第一个工厂、科学实验室、医疗中心、学校和社交中心。由于母亲的职能而产生的女性的权力和声望,在她们对社会有益的劳动活动的光荣记录中达到了顶峰。
男性的解放
只要狩猎是不可缺少的全职职业,它就把男性降到了一种落后的存在。狩猎旅行将男性长时间地从社区中心和更高层次的劳动的参与中剥离出来。
女性对农业的发现,以及对牛和其他大型动物的驯养,使这些男性得以从他们的狩猎生活中解放出来。狩猎随后被降低为一项运动,男性才得以在社区的生产和文化生活中得到教育和锻炼。由于食物供给的增加,人口也随之增长了。游牧营地被变成了定居的村庄中心,后来演变成城镇和城市。
在他们解放的第一个阶段,男性的工作与女性的工作相比,自然是非熟练的劳动。他们清除灌木丛,准备好供女性耕种的地面。他们砍伐树木,为建筑工作准备木材。只有后来,他们才开始接管建设工作——就像他们也接管了牲畜的照料和饲养。
但是,不像女性,男性不必从头开始。在短时间内,他们开始不仅从女性那里学习所有的熟练工艺,还开始在工具、设备和技术上作出巨大改进。他们开创了一系列新的发明和创新。随着耕犁的发明和家畜的使用,农业发展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在历史中的某个时间段,由于男性从狩猎中解放出来,两性之间的劳动分工出现了。男性和女性一起推进了食品和产品的富足,巩固了第一个定居的村庄。
但是,由妇女带来的农业革命标志着食物采集和食物生产时代之间的分界线。同样,它也标志着野蛮和文明之间的分界线。此外,它标志着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出现和两性在经济和社会领导角色方面的逆转。
新的条件,首先是食物对于不断增加的人口的充足,释放了一个新的生产力,以及随之产生的新的生产关系。性别之间的旧分工被一系列新的社会劳动分工所取代。农业劳动与城市工业劳动分离;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分离。女性的劳动力逐渐被男性取代。
例如,陶制轮的出现,男性专家从女性手中夺走了制陶业。正如柴尔德所写:
“民族志显示,使用(制陶)轮的陶工通常是男性专家,不再是女性,对于她们来说,制陶只是一种如烹饪和纺织一样的家务。”[39]
男性接管了由女性发明的烤炉和窑炉——并将它们发展成为铁匠铺和锻炉,在那里他们转化了地球的金属:铜、金和铁。金属时代是男性时代的黎明。而今天最常见的名字,“史密斯”,就起源于那个黎明。
正是带来了男性解放的那些条件,导致了母权制的颠覆和女性的奴役。随着社会生产落入男性手中,女性被逐出了生产生活、赶回到她们生育的生物功能。男性接管了社会的缰绳,建立了一个服务于他们的需要的新的社会制度。在母系社会的废墟上,阶级社会诞生了。
从早期社会制度中的女性的劳动记录中,可以看出两性在建设社会和推动人类向现在的阶段前进方面都发挥了作用。但是他们没有同时或一致地的发挥作用。这实际上是两性的不均衡发展。这反过来又只是整个社会不均衡发展的一种表现。
在社会发展的第一个伟大的时代,是女性把人类向前拉出了动物王国。由于第一步是最难的,我们必须重视女性的劳动和社会贡献视的关键意义。是她们在生产、文化和知识生活领域取得的成就使得文明成为了可能。虽然女性奠定这些社会基础花费了成千上万年,但正是因为她们如坚实和完善地奠定了它们,才以至于只花了不到4000年的时间就把文明带到了现在的状态。
因此,在实际的历史过程框架之外讨论男性或女性的优越性是不科学的。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性别的社会优越性曾发生过一次巨大的逆转。首先是生物学上被自然界赋予(优越性)的女性。然后才是社会上被女性赋予(优越性)的男性。理解这些历史事实是为了避免因情感或偏见而作出的臆断的陷阱。并且,理解这些事实是为了推翻女性生来比男性劣等这一谬误。
本文译自《第四国际》第15卷第2期,1954年春季刊。
原文链接: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reed-evelyn/1954/myth-inferiority.htm
[①] Robert Briffault, The Mothers: A Study of The Origins of Sentiments and Institutions, New York: The Macmillan, 1927, 3 vols.
[②] 《原始文化中女性贡献的份额》
[③] 《人类学》
[④] 同上。
[⑤] 《金枝》。
[⑥] 《法则和秩序的演变》
[⑦] 《人类学原理》
[⑧] 同上。
[⑨] 《历史上发生了什么》
[⑩] 同上。
[⑪] 《人类创造自己》
[⑫] 同上。
[⑬] 同上。
[⑭] 《医学的幼年》
[⑮] 同上。
[⑯] 同上。
[⑰] 《社会人类学导论》
[⑱] 《母亲》
[⑲] 《人类创造自己》
[⑳] 同上。
[21] 同上。
[22] 同上。
[23] 同上。
[24] 同上。
[25] 同上。
[26] 同上。
[27] 《人类创造自己》
[28] 同上。
[29] 同上。
[30] 为布里福特所引用,同上。
[31] 同上。
[32] W·斯科斯比和凯瑟琳劳特利奇:《与一种史前人在一起》
[33] 同上。
[34] 同上。
[35] 同上。
[36] 《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
[37] 同上。
[38] 《人类创造自己》
[39] 《历史上发生了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