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生态现代主义改良还是革命生态社会主义?
目录
[爱尔兰]保罗·默菲(Paul Murphy)
日土兀 译、Hertzian 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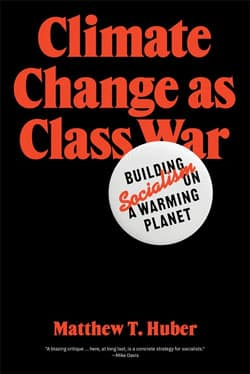
尽管书的标题是“气候变化作为阶级战争”,它无法抗衡资本主义生态灭绝的现实。这是一本具有两面性的书。
一方面是耳目一新的、明确地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及为利润而生产是气候灾难的成因。随之而来的是,认识到要抗衡气候变化是一个权力而非知识的问题,而且工人阶级是唯一有潜力去应对这危机的力量。而要去动员这股力量,作者胡伯(Matthew T . Huber)主张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这与我们这本杂志文章内提及的很多元素是共通的。[1]换言之,这是一个改善劳动人民生活的纲领,同时将我们的社会转换为一个百分百使用可再生能源的社会。
但另一方面则是对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众多方面的盲目。胡伯完全聚焦在气候变化及驱动它的化石燃料排放。他几乎全然无视当前九个限度中已经超标的另外四个。[2]同样对于全球南方,本书只向美国工人提供策略。这明显是刻意的短视,为的是强调他推广的生态现代改良主义的正确性,并反对生态社会主义去增长(ecosocialist degrowth)的概念。
阶级斗争生态学
胡伯的关键论点是“这有关气候变化的特殊权力斗争是一种围绕我们与大自然及气候本身的社会与生态关系展开的阶级斗争:所有制和对生产的控制”,[3]拒绝从个体消费行为背后去看创造了这个消费条件的,整个以利润为本的制度。
他恰当地驳斥了“碳足迹”背后的思维,这计算方式首先是作英国石油“超越石油”宣传活动的一部分被推广开来,目的是要为其“洗绿”。[4]它是要为当前全球正经历的气候灾难负责的“生产的隐秘之处”。消费者在作出选择前,大部份重要选择已经被人所决定——物品如何生产?生产什么物品?如何运输?如何销售。所有决定都是基于利润的最大化。
知识不是问题所在
胡伯也有效地拆解了“应对气候变化的障碍是缺乏知识”的想法。对在环境运动的我们而言,这想法仍然支配着即使是最激进的人。这种想法的其中一个方面是我们需要在气候变化议题上“唤醒人们”(让他们意识到)当前在发生什么事。此观念正是那些例如向梵高的油画泼汤的“停止石油”活动者们勇敢行动背后的基础,其思维是“如果人们知道了,他们或许会加入我们”。
另一个元素存在于无数环保人士之中,他们认为在生态危机的各个方面,只需要更好、更全面的政策。胡伯直率但精确地反驳道:“解决气候变化不需要更好的环保政策构想;我们需要更强大的工人阶级。”[5]
我们知道气候变化为什么发生,也知道如何阻止它。大型石油公司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知道气候变化并刻意把它隐瞒起来。[6]我们没有行动起来不是因为我们知道得不够多。而是因为这样做有损掌权的资产阶级的实际利益。
这不是要摒弃提高关于气候和生态灾难意识和觉悟的重要工作。人类整体对生态危机有巨量的知识,但基于资本主义底下工作生活的压力,可以理解的是,大部分人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带来的干扰的强度和广度,也不知道资本主义对当下为数百万人的生活,及不久后对我们所有人的生活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相反,我们要认识到传播知识需与对抗那些对危机负有责任者的大规模动员策略连结起来。
工人阶级作为改变的力量
胡伯论述的核心是呼吁建立“无产阶级生态学”(proletarian ecology)——以具有能力且利益相当的工人阶级为变革推动者,去迫使采取气候行动。为了动员这股力量,他主张“把对人民生活直接、实质的改善与气候行动联系起来”的策略,雄辩地主张“由此基础上,大量劳动人民或许会开始视气候变化为一个需要社会及政治上根本性转变的,以改善他们的生活的危机, 而不是要负担或习惯的成本。”[7]
这是切中时弊的,他在绿色新政的纲领中列出的部分诉求也是如此——免费公共房屋、融入绿色建筑实践、免费公共交通、医疗保健、粮食与房屋去商品化、更短的工时。读者会在我们爱尔兰社会主义组织RISE(按,其名称是“革命·国际主义·社会主义·环保主义”四个词的首字字母缩写,该组织参加人民先于利润党)的立场书(《我们的主张》)中找到以上所有内容。[8]
胡伯也提出了有说服力的呼吁,要策略性地聚焦在电力工人上。他主张要“让一切”目前直接需要化石燃料驱动的东西“电气化”。这包括大部分的家庭供暖、交通运输以及社会上大部分工作方面的能源应用。像爱尔兰人民先于利润党(People Before Profit)那样,他提出能源系统国有化,写道“只有公有电力系统会心怀长远基建——和环境保护——的目标进行投资和规划。”[9]
在那框架内,他主张在电工工会内采取一种平民化策略,推动他们为争取一个驱动电气化及开发再生能源的公有能源部门作斗争。如果社会主义运动家听从这个忠告,工会和气候运动会变得更强大。
一种阶级的教育性理论
胡伯对工人阶级的分析是极受欢迎的,但他对谁属于这阶级的定义却是明显地缺乏说服力。他声称采取一个唯物主义的立场,发展“一种对工人阶级的生态学定义,即一个不单脱离生产资料的阶级(正如我们常说的那样),且一个与生态生活手段(最明显的是土地)本身分离的阶级”。[10]
但这有前途且引人入胜的定义被置于一旁,实际被一种阶级的教育性理论所取代。他在描绘美国的工人阶级时引用了金·穆迪(Kim Moody)的杰作。[11]但他实际上没有依赖穆迪具体的分析方法,而是在计算方面抄了快捷方式,以证明全美有63%的人口拥有副学士学位(在美国是一种技术性的第三阶段(大学)教育)或更低的教育程度,并实际总结道这就是工人阶级。换言之,任何人拥有高于第三阶段(大学)学位就不属于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他正试图处理一件实际问题,即我们所有不持有资本的人,面对的剥削程度不同,感受到程度不同的主体性,遭受资本不同程度的控制。一个在政府工作的科学家为生存出卖劳力,但她更比一名星巴克咖啡店员工有更大的主体性。再者,在现今企业内还有一层管理人员,其角色是监督其它人的生产,并强化对他们的剥削。这群人形成了现今中等阶级的一部分,且往往具有较高的教育程度。
可是,他对此问题的解方是把大学学位塞给所有工人,把他们变成专业管理阶级。[12]尽管他认同穆迪的观点,即“很多专业职位正在无产化”,他基于“资格认证在他们进入劳工市场时扮演中心角色”的理由,[13]坚持强调他们与工人阶级其它分子的区别。
胡伯方法的问题在于他把受大学教育的每一个人都归入专业管理阶级,而没有进一步调查他们在生产中的角色及他们享有的自主性。这样,高级经理、社会工作者以及受过大学教育但低薪的办公室员工都被归类于“非工人阶级”的盒子里。[14]
这种把大学程度教育等同于中产阶级专业职位的方式,在三、四十年前或许是一种不错的速记方式。当近年平均教育水平急速上升,它肯定不再是(有效的)了。例如,在爱尔兰,三十至三十四岁的人中有46%具有第三级或最高学历程度,七十五至七十九岁以及五十五至五十九岁具有同等程度的人士分别有12%及22%。[15]在美国,尽管大学学费是天文数字,民众受教育程序也正稳步上升。[16]事实上,美国的工会成员受教育程度是不成比例的高,四成六人至少有一个学士学位。[17]
随着工人阶级的年轻人获得专上教育,然后获得工人阶级职位的情况日益普遍,在胡伯看来全球北方的工人阶级是否正在日益萎缩?
这种根据教育水平定义工人的见解(educational workerism)似乎有两重动机。首先,寻求把运动家指向那些在生产环节最具有潜力的工人,这是正确的进路。这些是可以通过罢工,把系统停下来(并导致资本家每小时损失数以百万计利润)的工人——例如石油工人、港口及货车司机,或日益普遍的物流业工人。其次,而且不幸地,它似乎是要透过暗示他们不是工人阶级,去削弱他眼中异见者的立场。
去增长
本书的大部分事实上是反对去增长的论述。虽然他承认去增长在气候正义运动内部有影响力,但他没有认真与主张去增长的左翼和社会主义者打交道,也没有诚实地把他们的观点提出来,也没有视之为有合法性的辩论。相反,他把推广这些想法的人的动机心理化了。因此,他这样写道:“从奢侈的生活方式的焦虑折磨引起的‘碳罪咎’的观点而论,‘减碳政治’在直觉上是具吸引力的。”[18]
他将“更多政治”的需求与之作对比。但这一点只是表面上正确,只涉及提出要求的方式,而无关内容。更少工作可以被说成是更多自由时间。要确保大幅减少私家车,需要更多公共交通。需要对公共房屋的更多投资,以确保减少隔热不良的房屋导致的碳排放。
胡伯谈到了事实上大部分人“对基本需要的增长有实际利益,像医疗保健、食物、交通,还有更多……”[19]但此这说法是一个假象的论点,因为在生态社会主义去增长的阵营中不会有任何人不同意这一点。
他根本无法与我们持有生态社会主义、去增长立场的人就我们所提出的核心论点打交道。为了确保人类一个宜居的未来,并为所有人——全球南方以及先进国家资本主义的工人、小农和原住民——确保合乎正义的过渡,必须减少总能源消费以及物质生产能力。这将涉及将军事及广告宣传方面的能源消耗降至零,大幅减少超级富裕者的能源使用,并增加全球南方的能源使用。然而他全然无视这一论点。我们必须假设胡伯的立场是人类可以在扩大清洁能源及民主计划的基础上,提高总能源消费以及物质生产能力。
在一本以唯物主义方法为荣的书,对客观事实的完整性忽视,是胡伯的分析与方法中的缺陷核心。他几乎忽视了其它已经被摧毁生态的资本主义冲破的地球环境安全界限。在他关于“氮资本”及其资本主义农业扮演的角色的优秀章节中,压倒性地聚焦在农业转型对碳排放的影响。虽然他确实提到人类超越了天然的氮循环,[20]超越了公认的地球界限。[21]但他甚至没有提到土地的使用变化,通常与耕作有关,是生物多样性消失的主因。[22]
大概率因为胡伯只关注于美国及气候变化,使之觉得大可忽略由于大幅扩大清洁能源进行的必要开采导致的巨大人员与环境成本。生产清洁能源几乎被当成是毫无代价的。虽然风能、太阳或潮汐能源确实没有成本,但是兴建太阳能板、风车以及锂电池却绝对并非如此。对稀土及矿产不加限制的开采会把我们进一步推过其它地球界限,摧毁环境以及数以百万计人的生计。这些人绝大部分生活在占全球75%人口的全球南方,而非生活在占全球人口25%的全球北方。
这是为什么生态社会主义者应该主张减少能源使用的同时,还要尽可能以冲击最小的方式发展可再生能源的两个关键原因之一。另一个不过是简单数学式的事实,即能源使用量越增加,要迅速提高可再生能源生产使之能及时达致完满的过渡就会变得越困难。
生态现代主义改良
把革命社会主义从改良主义者中区分开来的一个主要观念是,马克思在1871年巴黎公社学到的深刻洞见,即“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23]换句话说,正如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解释道[24],国家不是一个中立的体系,工人阶级能像资产阶级那样把它用得一样的好,来实现自己的目标。相反需要把它摧毁,代之一个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以服务掌权的工人阶级的利益。
不幸地,同马尔姆(Andreas Malm)[25]一样,胡伯似乎也把这分析搁置一旁。他们的视野局限于向现存的资本主义国家施压去做必要的事。胡伯正面引述了帕伦蒂(Christian Parenti)在《雅各宾》的文章:“只有国家有力量去驱动这样的能源转型……但……没有庞大的自下上的民众压力,国家不会这样做。”[26]
在这一点上,绿色新政在爱尔兰杂志《Rupture》主张的生态社会主义与胡伯所的主张分道扬镳了。他的主张是试图向现存的资本主义国家施压去做必要的事。他对罗斯福的“新政”持肯定态度,没有提及它事实上是挽救而不是克服资本主义的尝试,而且其产生利益的分配的不成比例且带有种族色彩。[27]
我们的策略是建设一种生态社会主义运动,使之有力推翻并解体现存的资本主义国家,代之以真正民主、参与性的工人国家。这并不代表我们不会对现存国家要求改良,但那些改良是出于现存的工人阶级运动,我们寻求一个能够结束资本家统治并推翻他们国家的革命运动。
相对于与国家的关系,这种改良主义对科技也采取类似态度。胡伯自认是一位社会主义生态现代主义者。换句话说,他视科技进步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工具。
他这样做排斥了更新近的洞见,即工人阶级不能掌控国家,与之相似,工人阶级也不能掌握在资本主义底下发展出来的生产力。[28]马克斯·阿吉尔[29]、凯·赫伦[30]、马尔姆[31]以及其他人都有力地指出我们所发展的科技充斥着把它创造出来的资本主义关系。
与国家的平行到此为止,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明显不会试图“粉碎”我们继承的技术。但它的确指出需要拒绝一种假设,即生态社会主义会沿着资本主义提出的技术发展路线走下去。
马克斯·阿吉尔(Max Ajl)在他《人民绿色新政》(A People’s Green New Deal)极其尖锐地把这个观点提了出来:“机会主义者、改良主义者、社会民主派立场的共同点,是对科技的盲目信仰,一种具魔力的催化剂,在现有制度下洒下星尘就可以把它转营成一个正义、可持续的世界生态。”[32]
给个具体的例子,看看“绿色革命”背后的技术发展。他们被呈现为巨大的进展,使世界摆脱饥饿。事实上,正如凯·赫伦所说的,其“主要的成就是慢性的过度生产,其核心是投入生产的利润,小持分者独立性的丧失以对共产党和农民土地改革抗争的镇压。”[33]
胡伯对在农业范畴内氮资本的批判是杰出的,但他并没有提出工业化农业的替代方案。他的确在其它地方[34]明确反对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在农业方面会减少资本密度,并相应增加劳力密度的想法。
这表明胡伯主张的那种“大就是美”的社会主义。他所呈现的社会主义持续了资本主义的路线,只是代之以公有制和可再生能源。马克斯·阿吉尔尖刻的评论道,这是“没有改变的改变”。[35]
这很大部分是朝向第二国际的进化社会主义的倒退,其核心是普罗米修斯式的进步观,视大垄断体的发展是“为生产的社会组织预备的”道路,[36]却缺少了从根本上与资本主义决裂的视野。这种普罗米修斯式的进步观甚至还没有被很多第三国际思想家一致抛弃。[37]
可是,如今当我们被淹没于生态崩溃的症状时,我们需要以革命生态社会主义来坚决打破我们传统的那些面向。我们需要摒弃把发展生产力等同于生产更多商品与服务,以及使用更多采自地球的能源和原料。
相反,我们可以从马克思的愿景中获得启发,在一个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到“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38]换言之,生态社会主义的视野是,当我们寻求抚平人类与非人自然之间的裂口,并确保地球上每一个人都能过上有质量的生活时,生产的本质也将发生转化。
胡伯的书是一本值得阅读和思考的书。它将向气候变化活动家指出正确的方向——面向工人阶级以及动员其力量对抗资产阶级的任务。可惜的是他以美国为重心的生态现代主义阻止了他发展需要的无产阶级生态学。
胡伯在关于需要一个绿色新政式纲领[39]去动员工人阶级人民为其客观利益斗争,改善生活水平,并应对气候危机这一点上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无需也不应把社会主义的视野窄化到一百年前界定的范围内。要避免任何类型的社会及生态灾难,需要一个生态社会主义纲领,结合去增长的洞见,以及革命的策略,去驾驭全世界工人及受压迫者的力量,推翻资本主义,为人类开创一个自由的新领域。
2023年6月13日
原文链接:https://climateandcapitalism.com/2023/06/13/ecomodernist-reforms-or-revolutionary-ecosocialism/
[1] 例如Diana O’Dwyer,《社会主义绿色新政的理由》,2020年第一期。
[2] 地球环境安全界限的框架表示了人类定的“安全生存区域”,是相对新的(2009年被提出),部份限度尚未被辨识,是否再添加其它限度也正处于辩论中。目前研究认为我们在目前也知的九个或者十个范畴中,已经有五个或者六个超越了限度:气候变化、海洋酸化、大气平流层臭氧消耗、生物地质化学循环中氮、磷循环、淡水使用、土地系统变化、生物多样性、化学污染以及大气气溶胶负荷。
[3] 胡伯:《气候变化作为阶级战争》,维索图书,2022年。
[4] 胡伯:《气候变化作为阶级战争》,第13页。
[5] 胡伯:《气候变化作为阶级战争》,第294页。
[6]本幻灯片杰出地勾勒出埃克森美孚研究以及掩饰气候变化的历史。 www.europarl.europa.eu/cmsdata/162144/Presentation%20Geoffrey%20Supran.pdf
[7] 胡伯,第198页。
[8] letusrise.ie/what-we-stand-for
[9] 胡伯,第241页。
[10] 胡伯,第46页。
[11] 金‧穆迪:《论新地景》,干草市场图书,2017年。
[12] 这个词汇在1977年首先由Barbara 和John Ehrenreich在《激进美国》的一篇题为《专业—管理阶级》的文章中提出。
[13] 胡伯,第118页。
[14] 我们甚至不清楚胡伯是否把教师视为工人阶级。他正面地评论教师罢工,但在第184页又写道:“在某程度上某些社会工作者和教师可能会对他们工人阶级客户及其子女表现不满,工人阶级也有很好的理由以同等的力量去响应他们。”
[15] cso.ie/en/releasesandpublications/ep/p-cp10esil/p10esil/le/
[16]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2010年至2019年间,25岁及以上获得学士学位或更高学历的人口比例,从29.9%跃升至36%。”
[17] 经济政策研究所资料表:《谁是今天的工会工人?》,2021年4月21日。
[18] 胡伯,第147页。
[19] 胡伯,第170页。
[20] 胡伯,第91页。
[21] 斯德哥尔摩韧度研究中心:《地球的九个界限》。
[22] 世界自然基金会:《Living Planet Report 2020》。
[23]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71年。
[24]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8年。
[25] 这明显在马尔姆具启发性的《如何炸毁一条输油管》(How to Blow up a Pipeline,维索图书,2020)可以找到。
[26] 胡伯,第69页。
[27] 胡伯,第218页。
[28] 米凯尔·洛威在他的《生态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灾难激进的另类选择》一书中对此概念进行了探索(干草市场图书,2015年)。
[29] 马克斯·阿吉尔:《人民绿色新政》,冥王星出版社,2021年。
[30] 凯‧赫伦:《The Great Unfettering》,新左翼评论,2022年9月27日。
[31] 马尔姆(Andreas Malm):《化石资本》,维索图书,2016年。
[32] 胡伯,第9页;马克斯·阿吉尔:《人民绿色新政》,冥王星出版社,2021年。
[33] 凯·赫伦:《The Great Unfettering》,新左翼评论,2022年9月27日。
[34] 胡伯:《生态社会主义:反乌托邦的和科学的》,《社会主义论坛》,2019年冬季。
[35] “没有改变的改变:生态现代主义”是阿吉尔《人民绿色新政》第二章的标题。
[36] 胡伯,第3页;考茨基:《通往权力之路》,1937年。
[37] 这一趋势的恶劣例子,见诸于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的第八章,在那里他主张“信仰只给了移山的许诺,那么,什么也不‘信仰’的技术则真的能开山劈岭。迄今为止,这种事为了工业的目的(矿井)或交通的目的(隧道)已经做了;将来,它还将按照整个生产和艺术规划的设想在无比广阔的范围内进行。人将着手重新勘测山川河流;并将严肃地、不止一次地修正大自然。最终,他将改造地球,即便不是按照自己的样子,也是遵循自己的趣味。我们丝毫没有理由担心,这趣味会是低级的。”
[38] 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1846年。
[39] 我们应该对超越“绿色新政”这一称呼持开放态度,因这一词语正日益被资本主义政府招安了(例如,欧洲绿色新政),当然也消除了其激进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