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软埋》是为了社会主义么?
藏器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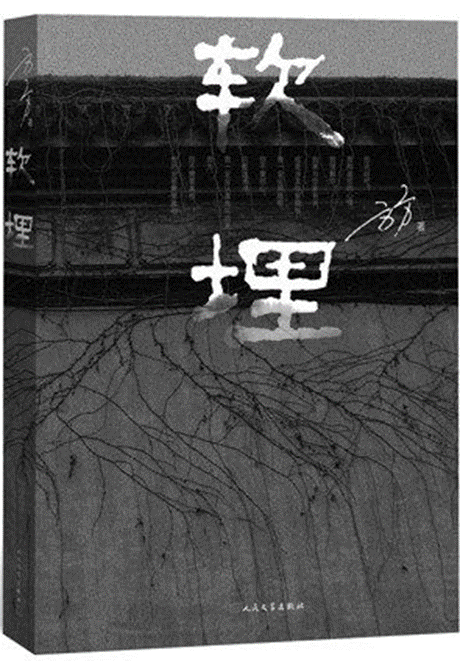
方方的《软埋》于2016年6月出版,在出版后还受到体制内一些官员和学者的赞许。不过自2017年以来,《软埋》遭到了很多所谓“左派”人士的集体攻击,这其中有郭松民的《土改绝非“灭门运动”——再评方方女士的〈软埋〉》、《什么力量捧红了方方和〈软埋〉——五评〈软埋〉》,老田的《告别革命之后的文学想象力问题—评方方的土改题材小说〈软埋〉》,丑牛的《〈软埋〉的是革命》、《方方同志仍在玩〈软埋〉》、《三读〈软埋〉——在武汉工农兵批〈软埋〉座谈会上的发言》等,高殿杰的《方方〈软埋〉到底要“软埋”谁?》,李北方的《〈软埋〉要埋葬的是什么》,王诚的《颜色革命的信号弹,〈软埋〉是要埋掉新中国》,曹征路的《从〈秧歌〉到〈软埋〉,将历史虚无主义进行到底》,甚至还有前中组部部长张全景的《〈软埋〉是新形势下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反映》,等等。
这些文章多数对《软埋》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其中最重要的是政治方面的批评,且均扣上了极严重的帽子。如王诚的文章中指出方方是要“颠覆新中国”,“背后绝对有境外反华势力的支持”,且犯了“颠覆国家政权罪”;丑牛则称“《软埋》是要埋葬共产党的革命,《软理》是‘还乡团’的叫嚣”,并称“西方反华、反共势力,已经在向你(指方方——引者注)招手了”;张全景称《软埋》的出现“是新形势下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反映”。这种指责明显已将方方称作“阶级敌人”,称为“罪犯”(而且是最严重的政治罪)。但绝大多数攻击并未仔细谈到文本,而且如“文革”时多数的大字报一样,尽量帽子优先,至于实情,往往不被写作者关注。因一些攻击文章被删,这些作者自称不断受到方方背后的势力阻挠与迫害,但这难道不正是当前体制下缺乏言论自由的常态么?再者,讨伐者最终实现了一个目的,《软埋》最终被禁,从各个书店下架。此后,这番口诛笔代才有所消减。
一、《软埋》是为了反对土地改革吗?
众多攻击文章均称《软埋》是为了反对土改,是出于政治目的反对革命叙事,是为了旧地主阶级招魂。如丑牛称“方方的《软埋》把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写得罪恶滔天”[1]。老田称:“而统治阶级缺乏觉悟的情况至今少有改变,方方作为地主阶级的后代,非常理想地继承了这一阶级的顽固守旧心态……”[2](老田在这里算是祭出了“血统论”的老调!)赵可铭称:“《软埋》极力美化地主阶级,否定土地改革的合理性。”[3]曹征路在其文章开头即指出:“(《软埋》的)内容是颠覆新中国的土改乃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历史……”[4]
但《软埋》中是否真的如此恶毒地攻击土改呢?《软埋》中确实对主人公丁子桃(原名胡黛云)的人生经历充满同情,对当年部分地区土改的过火行为有所指责,但这是否够得上反对土改,就要就其文本来细说了。
方方本人曾在武汉运输合作社中工作,后来因考上大学方才脱离底层,但这样的经历促使方方写出很多反映底层生活的作品,如《春天来到昙华林》、《万箭穿心》等,她自己也曾说:“有时候,我们在写底层人生活的作品时,我们容易有居高临下的同情心。我觉得这样真的很伤害人。其实,底层人需要的是真正的尊重,对那些高高在上的同情姿态,他们甚至很厌恶。”[5]当然,一个人书写底层,未必等于自己就是社会主义作家。方方的笔触也主要是出于一种人道主义情怀,与“革命”、“社会主义”等本无什么关联,我们也找不出她自己在什么地方自称社会主义者。“底层”本身与工人阶级等概念之间不可划等号。她创作《软埋》,大体仍是出于这种反映底层的想法。主人公丁子桃(胡黛云)虽然在新中国前是人上人,但在新中国时期(在其子立业之前)则是底层——这里有两种概念的底层,一种是其“当下”身份,如做军事首长家的保姆;另一种是隐含在记忆中的身份,即她其实是隐藏的政治贱民(地主成分,这在毛时期是“黑五类”)。既然如此,在共产主义者眼里也就没有必要要求她以一个社会主义者的身份来写作,并在作品中充盈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如果真要求她这样一位非社会主义者依社会主义的思想写作,岂不是非要人写违心的作品,去说假话不可么?即使一个人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也应有权创作并非反映革命的作品(只要不是反社会主义的)。
《软埋》描述了个别地区土改的残酷性一面,包括有的地主及家人被迫自杀,有的被以残忍的方式处决等,一些人以此来判断《软埋》是反土改小说,则未必过于苛责,因为土改本身是否合理,并不在《软埋》的考虑范围之内。不过《软埋》在刻意营造历史大势的不可抗拒和小人物在历史大势中的悲剧。《软埋》中的历史大势即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命运”,这通过小说中对将军刘晋源的描述呈现出来。刘晋源与自己的妻子的宅心仁厚,刘晋源的儿子在商业上的成功,刘晋源寻访革命战友李东水等,既是对当下统治的一种认可,也是对当下执政者获取统治的历史的正统性的认可。丁子桃儿子在事业上的成功(如为母亲购买别墅),更是隐含了作者对当下改革开放政策(即当下政治合法性)的认可。
而《软埋》在对小人物的描述中,也并未对地主阶级作过于理想化的书写,相反在很多地方展现出他们的不足,并写出导致其最终覆灭的“原罪”。如陆氏一家是靠贩鸦片起家;陆家为了得到金点家的田地,趁金点母亲即将临盆之际以借车为名强迫金点父亲卖地;这便是陆家的“原罪”。如失忆前的胡黛云(丁子桃)本性自私,且鄙视穷人,自认为“穷人和富人,永远不可能有平等”[6],阻挠长工金点与陆家小姐陆慧嫒的结合等;这又是丁子桃的“原罪”。这些“原罪”构成方方对地主阶级统治方式的一些感性认识。但丑牛在《〈软埋〉的是革命》中称:“几千年来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暴统治,方方一点也看不见。”或如李北方所言:“方方把地主的大家庭写的温馨又和睦,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长工丫环忠心耿耿。”[7]则要么难免让人怀疑对方是否只是看了几页便难以抑制心中的愤怒,要么只是为了攻击而不顾事实。各位“左派”对方方《软埋》的指责是“反革命”,但在小说文本中我们至多可以看到方方并非革命者,毕竟“反革命”与“不革命”之间还是隔若天渊的。
总之,依照这些“左派”人士的话语,对出身自地主的小人物在历史大势面前的悲剧命运稍显同情,那就是向“旧社会”,向地主阶级显示忠诚,那么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中以一个屡次反叛苏维埃的格利高里为主角,也难免是要搞反苏维埃的“历史虚无主义”了。
二、土改中的暴力与文学叙事
很多批判《软埋》的文章都花了大笔墨来写土改的正义性、历史必要性。作为共产主义者,自然反对前资本主义式的各种土地所有制与农业剥削制。实现耕者有其田是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内容,也是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农业合作化开展的重要前提。革命可以尽量减少暴力,也应该尽量减少暴力,但无法彻底避免暴力。因为统治阶级掌握国家暴力机器,被剥削者与被压迫者在反抗时难免遭到暴力打压,在此情况下,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就难免要用暴力方式来反抗(当然,像十月革命那样通过很少的暴力即推翻临时政府是非常理想的状态)。中国大陆在土改时会面临一些地主武装的反扑与抵制,这时发生暴力也本无可厚非。但对一些无武装的地主滥施暴力,则属于一种多余的暴力,它不会让农民真正觉醒起来,而只会给革命带来负面效果。
抗战结束后的土改中,暴力的发生有两次高潮,一次是1947年一些老解放区的“左”倾土改[8],二是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的新解放区部分地区的暴力土改(当然国内多数地方的地主未被处决,但个别地方处决、被逼自杀等情况很严重)。老解放区的“左”倾土改在几个月后由于中共中央的纠偏工作而停止,新解放区的则断断续续持续到了1951年,而“地主”、“富农”的身份直到1979年方才解除。
指责《软埋》的人称土改中并无《软埋》中描述的那些暴力行为,更无导致人灭门的惨案发生,因为称《软埋》是搞“历史虚无主义”(按字面意思,即否定历史真实)。如老田说:
这第三波土改,都是由老解放区参加过土改的“南下干部”主持,经验较为丰富,而且早期土改中间引发过火暴力的“挖浮财”问题,此时也都有了明确的政策界限。新解放区土改有着非常确定的顶层设计,而且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有组织的运动,还是由有经验的土改干部主持进行的,这是确凿无疑的。方方的小说所说的由村子里的冤冤相报来决定地主的生死,是彻头彻尾的想当然。
又称:
方方所设计的讲故事情节中间说,村子里工作队某人就能够决定地主一家的生死,斗争会上人还可以任意打人甚至打死人,基于这样的信息,就有地主作出决策要进行决绝的反抗——软埋自己和家人。据老田访问所知这绝对是不可能存在的。不仅新区土改有着明确的政治建设的目标,而且具体操作方面死刑批准之权都在地委级别……[9]
又如张全景称:“南方新解放区的土改充分吸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掌握政策比较稳,即使执行镇压反革命的政策也是比较稳妥的,没有乱打乱杀了。”李北方甚至称:“其实,历史的真实是,地主不但不会被灭门,还会被保护得很好,留着当反面教材,用于激发和培育翻身农民的阶级意识。”至少从老田、张全景和李北方的论述中,新解放区的土改更加规范,少有或没有暴力现象。即使有,也受到严格限制。且土改就是中共当时已经完美设计好的一场运动,一场完全符合阶级斗争路线的运动,一场借土改来报私仇是情况是不可能存在的运动。如此一场完美无瑕的运动,恐怕只会存在于大脑中。而老田以当时死刑核准权在地委级别,在一些时间在县级,而否认滥杀的可能性,也是完全不顾历史现状的胡说。当前为了防止死刑的滥用,死刑核准权在最高法院,而在死刑核准权在省级单位的八九十年代,一遇各种“严打”时,各种误杀、滥杀尚不能避免,更何况是在地委级或县级?当中央政策中对滥杀的管控稍有放松时,实质上由工作组决定处决人的事情就难以避免(死刑核准就成为一种形式)。
也有人称暴力仅限于施加在一些罪大恶极的地主身上,如王诚称:“这种血海深仇难免在群众当中,产生过激情绪,有一些罪大恶极的地主阶级被愤怒的民众判处极刑。”[10]这一条算是对老田说法的否定,当然也不是没有问题。有时土改时的极左措施实行时,一是死刑范围容易扩大,土改中对地主的暴力殴打难以完全避免;二是容易错划成分,即将更大范围的人划入地主或富农,这不仅存在于中国,也存在于学习中共的缅共的土改中[11]。
新解放区土改中的暴力事件当然不是全国均衡暴发,而丑牛举鲍家村,老田举湖北个别地区的土改来说明新解放区土改不存在那种灭门性暴力,本身不值得推敲,也没有任何学术基础。在此转引杨奎松论文中的数据,来专门说明川东土改的暴力事件:
营山县30%的村子发生了吊打和肉刑的情况,全县被划地主多达3760户,其中自杀了261人(总共自杀301人)。荣昌县七区4个乡,54个村,共划地主663户,3376人,区领导自土改开始,便放手组织乱打、乱吊。14村共划中小地主15户,就打死了15人,平均每家一个。土改干部林成云在斗争大会上甚至用刀割断了被斗地主的脖子,众目睽睽下当场将地主杀死。由于地主成为受辱和死亡的代名词,一些农户得知被划为地主后,竟绝望自尽。有地主生恐被斗,硬被拉到斗争会场后,即用头当场撞柱而死……[12]
营山、荣昌均属当时的川东地区,与《软埋》中所描述的地区大体相合。其实哪怕只有很少数地区发生了类似的滥杀与暴力事件,那它就首先是存在的,而在文学叙事中加以描述,就谈不上是歪曲历史,搞“历史虚无主义”(从“历史虚无主义”的字面意思上讲),相反比起这些攻击者来,要更加尊重历史。
而文学中涉及土改时,无论从贫农角度还是从地主角度切入,无论是表现其中的阶级关系还是展现小人物的悲剧命运,或是底层人对高贵者的讽刺,均是文学创作的一种自由。文学毕竟不同于政治,政治叙事往往要有明确的阶级立场,会存在遮蔽,而文学甚至有义务揭露出那些被遮蔽的部分,以更充分展现历史大潮变化中人的复杂性。因《软埋》对这种人的复杂性进行了提示而对其怒气冲天的人,他们只需要一种被统治者完全规训的文学,那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式的典型描写。曹征路所言正是这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式的批判:“通过‘个人化的历史’‘虚无感的历史’‘戏说历史’来替换客观实在的真实历史。”但历史不可能只有那种宏大叙事,小人物同样构成历史的方方面面。之所以会对“个人化历史”如此反感,正在于这是对官方营造的国家主义的宏大叙事、整齐划一阐释的“解构”。
且事实是,即使这些攻击者们口口声声所谈的阶级意识,也是被他们“理想化”的,而非阶级常态。如李北方称:
方方把地主的大家庭写的温馨又和睦,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长工丫环忠心耿耿。胡如匀的小老婆死心塌地跟着胡家不肯被“解放”,陆子樵家的下人宁可跟着东家一块服毒自杀,也不肯迎接穷人翻身的新社会,前面提到过的富童没有死,直到吴青林去寻访的时候,他还在疯疯癫癫地给陆老爷看坟。[13]
方方既然不是社会主义者,本没有义务去揭示前资本主义的人身依附关系及其心理表现。那种“温馨”与“和睦”自然是宗法大家庭下的表象,而且不是全部,至少金点脱离陆家后就选择了复仇,而不是继续忠于自己的主人。而其他人如富童显然保留着阶级意识未曾萌发前的那种对东家的忠诚,胡如匀的小老婆也没有独立的女性意识,而是还保留着那种旧式的父权观,这是人身依附下的常态。如果一定要把各位长工丫环和小老婆都写得立马欢迎解放,与东家作阶级斗争,才是与事实相违背的事情,否则还要共产主义者的群众工作干什么?群众的觉醒需要过程,不是处于被剥削者或被压迫者地位的人就天然具有阶级意识,像前资本主义下的人身依附与“忠诚”,正是阶级社会秩序的一种意识形态保证。在这方面,方方写得恐怕更符合历史(当然,非革命者的方方不会重点写出革命的具体发动过程)。
三、反《软埋》运动与社会主义无关
近几年来“反历史虚无主义”的风气很盛,攻击《软埋》的人多数是出于“反历史虚无主义”的政治诉求而谈的。不过在此也可以看一下各位义愤填膺地“反历史虚无主义”的人的目的是什么,是否如他们口头所说是为了工农的利益,是为了反对剥削阶级呢?
如王诚的话就明确阐述了自己的阶级性:
正是因为中国农村以极低的成本培育了大量的相对高素质劳动者,才使得中国的人口红利源源不断地释放出来,通过与全球产业链的结合,把中国变成了世界工厂,尤其是加入WTO以后,短短十几年,崛起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强国。这一切都要得益于中国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度,没有这个制度,我们哪里来那么多“廉价劳动力”?哪里能支撑起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14]
王诚的重点是落在经过土改和集体化的中国能提供更多“廉价劳动力”上,然后靠着这廉价劳动力,可以增强国力。而与“廉价劳动力”相对应的,正是资产阶级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加重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尽量削减支付工人阶级的工资。
王诚还称:“我们今天的基础设施建设之所以能完爆印度,甚至在许多方面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就是得益于我们的农村土地所有制度,国家得以用较低的补偿,通过政治动员,快速立项上马,快速开工完工,为中国经济的起飞奠定基础。”[15]这一点正可以和列宁的一段论述相合:
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实行这种改革有没有可能呢?不但有可能,而且是最纯粹、最彻底、最完善的资本主义……土地国有化能够消灭绝对地租,只保留级差地租。按照马克思的学说,土地国有化就是:尽量铲除农业中的中世纪式的垄断和中世纪关系,使土地买卖有最大的自由,使农业最容易适应市场。历史的讽刺在于:民粹派为了“防止”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竟然实行一种土地纲领,它的彻底实现会使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得到最迅速发展。[16]
而中国土地集体化和国有化在资本主义复辟时代正与这种土地国有化的结果相类似(联产承包责任制并未改变产权上的集体所有与国有性质,且对一些国有企业取消了绝对地租),即事实上大大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因而其着眼点并未放置在工人阶级与贫农身上,而是放在新兴资产阶级的成长上。
大体这些攻击者也自称支持马克思主义的,而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里国家(state)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而他们会提出怎样的要求呢?老田认为:“最理想的状态,还是精英阶层自己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回头反思自己,重建与民众的有机联系,再生产国家和民族认同,这是今天精英阶层寻求自身未来统治地位的最合理努力方向。”潜台词就是像方方这样的人缺乏“国家和民族认同”,而他们现在要做的是找到国家与民族认同,路径是“重建与民众的有机联系”,似乎这国家与民族就是民众的民族与国家。但国家给民众带来什么呢,国家如何去解决工人受剥削的现状呢?这正是要向老田追问的问题。更何况在马克思主义观念里,社会主义正是要建立无国家的社会的,而非加强国家与民族认同,老田的方向倒正是逆社会主义而行的。
当然,与攻击者非黑即白的态度不同,笔者也不是说因攻击者不代表社会主义,方方就代表社会主义了。方方作品中并不能看出她就是社会主义的支持者,她也确实享受着当前体制的一些好处,她的生活也确实优越。但以一些知识分子物质生活优越,享受体制内特权为名,来对其加以迫害与攻击,尤其是从此限制其创作自由,不正是以文革式“造反”来打压创作自由的方式么?事实上,物质的不平等只应由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工人民主的普遍施行来改变,像各个攻击者那样在不主张根本变革当前生产关系的前提下来高喊“平等”,来“打倒权贵”,不过是扶植新权贵反对旧权贵的路径而已。放在文艺领域,不过是换上听话的自己人做文艺界新特权者,以扳倒现在享有特权的人而已。在新权贵产生的过程中,必定要通过更严厉的文艺管控来压制异见方可实现,如张全景建议的:
建议有关部门成立两个调查组,一个调查组去找好作家、好作品,找准了就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表彰;一个调查组去找创作倾向与中央对着干的作家作品,找准了就旗帜鲜明地予以批评。这才是真正做导向工作。[17]
如今在中国有几人的作品敢“与中央对着干”呢?大体即使有这样的作品也根本无法过审。所以这种建议不过是要找一批不完全作中央宣传文稿的作品大加批判而已。如此一来,恐怕真的是在文艺界要所有竹子一样高呵!
小结
总之,攻击者刻意使用“历史虚无主义”来给《软埋》定性,其目的不过是媚上而已。毕竟中共中央数次提及要“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软埋》又正好涉及历史问题,一群人就利用此定性发难,并最终促使《软埋》被禁。这种种批判方式与批判用语与毛时期发起的历次文艺批判风潮非常接近,不必考虑事实,只需迎合圣意;不求文艺创作自身的规律,只求制造冤案以起震慑作用。攻击者在批判时列了一系列创作标准,只不过是要强调政治决定文艺的官僚主义创作路线而已。他们那里无论从哪方面都看不到社会主义的光影,只看到国家主义的鬼魅在晃动。这国家主义的政治化创作标准,今天针对的是《软埋》这样一部涉及敏感历史议题的作品,明天必将扩大到对其他作品的批判当中。这些国家主义者想做到现在的国家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打着“非体制”、“非官方”、“底层”、“工农”的旗号来号称自己代表民意。
但目前绝大多数参与到批《软埋》(不是指一般的文艺性批判,特指本文所批判的这种政治化批判)运动中的人绝不会是工农之友。当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解放区文艺创作之风便趋紧,如今的国家主义者想要的甚至都不带进步的影子!更何况对工农而言,自由的创作才能更好激发自由的精神。不论方方不是社会主义者,不论《软埋》不是革命文学,方方的创作与《软埋》发行自由均不应被限制。依靠媚上来达成自己的钳制文艺自由的目标,正显示出国家主义者本质上的虚弱无力。
[1] 丑牛:《〈软埋〉的是革命》,http://www.wyzxwk.com/Article/wenyi/2017/03/377708.html
[2] 老田:《告别革命之后的文学想象力问题—评方方的土改题材小说〈软埋〉》,http://jiliuwang.net/archives/49787
[3] 赵可铭上将:《〈软埋〉是对土改的反攻倒算》,http://www.szhgh.com/Article/wsds/wenyi/2017-05-24/138253.html
[4] 曹征路:《从〈秧歌〉到〈软埋〉,将历史虚无主义进行到底》,http://www.wyzxwk.com/Article/wenyi/2017/04/378532.html
[5] 方方:《我为什么一直在写底层》,http://cul.qq.com/a/20150626/035805.htm
[6] 方方:《软埋》,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第274页。
[7] 李北方:《〈软埋〉要埋葬的是什么》,http://www.cwzg.cn/politics/201703/34603.html
[8] 丁子桃丈夫吴家名家人被处决则属于这一波暴力土改潮。
[9] 老田:《告别革命之后的文学想象力问题—评方方的土改题材小说〈软埋〉》,http://jiliuwang.net/archives/49787
[10] 王诚:《颜色革命的信号弹,〈软埋〉是要埋掉新中国》,http://www.szhgh.com/Article/opinion/zatan/2017-05-30/138702.html
[11] 可参考李必雨:《亡命异邦——缅共游击队十年亲历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
[12] 杨奎松:《新中国土改背景下的地主问题》,《史林》,2008年第6期。
[13] 李北方:《〈软埋〉要埋葬的是什么》,http://www.cwzg.cn/politics/201703/34603.html
[14] 王诚:《颜色革命的信号弹,〈软埋〉是要埋掉新中国》,http://www.szhgh.com/Article/opinion/zatan/2017-05-30/138702.html
[15] 同上。
[16] 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列宁全集》(第二版),人民出版社,第21卷,第431页。
[17] 张全景:《〈软埋〉是新形势下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反映》,http://www.szhgh.com/Article/wsds/wenyi/2017-05-22/138125.html
